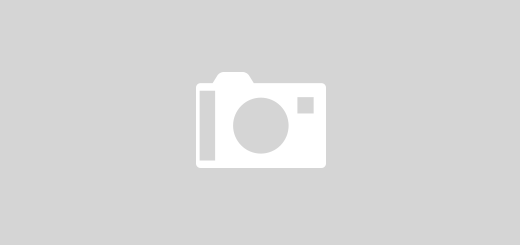蜕变的黑色情人(1)
乌黑缎衫,相当漂亮考究,特意在那两管袖子边缘,用挺薄的纱料绾结,手工压出明暗鱼鳍纹路。用张爱玲的话说是,“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香颂觉得自己就是这件衫,黑得不见天日,黑得明珠暗投,黑得非常盲目,黑得十分浪费。
黑色缎衣
过年,众人穿红的绿的,香颂穿黑。
寒凋凋的黑,沉甸,严厉,像一场刑。
张爱玲说,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不对,这话明明是张爱玲的姑妈说的!”香颂反驳纪恩时,总是仰着脸,似乎有所求。那样的眼睛,黑白分明,不染红尘,特别像一个小孩。看到这样的女人,纪恩便没有办法,只好任由她麻烦到一丝不苟。为了一件衣服,她要他陪她跑大半个城,挖空心思找到上海裁缝店,大半天已经耗掉。
对襟乌黑缎衫,璎珞矜严,正当心的金补字,绣的不是龙凤鸳鸯,不是花草牡丹,而是一只毛憨憨的大麒麟。尾巴上挑出一朵桃红绒球,眼珠位置嵌两枚雪白珍珠,麒麟本是神物,目光傲岸苍茫。
胭脂路的上海裁缝,非常势利,笑脸给老外,白眼给国人,可是,他们的手艺实在好,料子实在是没得挑。香颂抚摸那匹黑色柞蚕缎,它如流水般柔软。“就这个了!”香颂低三下四跟裁缝店那帮小人讲解,要什么款式,要什么图案。
其实香颂并不爱唐装,这些年来她所钟情的,是三宅一生的简阔,抑或小筱顺子的未来主义、太空风貌。贝壳、海藻、石头,纸、绢、棉、竹,都敢往身上披挂,幻化成缠裹和重叠的姿态,方是香颂的最爱。
可是这一年不一样,她要一种新格调,衬她收获的新感情。
纪恩被香颂烦不过,坐在车里直按喇叭,催道:“香颂,快点,再不出来,年都要过完啦!”
大年三十,暮色四合,淡淡地,开始落雪。
现在的春节早不作兴放鞭炮了,但街上还是有小孩子在点燃一颗颗小爆竹。从香颂公寓的12楼听下去,零星的爆竹在有雾的街道响起,像一池温吞的洗澡水。香颂觉得乏累。
香颂泡好一壶茶,拿眼衔着纪恩。她在观察她的这个男人,在这个晚上,他又焦躁又溃败,又无奈又狼狈,以往刚强的样子全不见,他只是搓着手,看着这年,马上要来了。他心里急。
可她偏偏不放他走,他又没有勇气直说“我得回家过年”,却又毫无留下的诚意。
然而除开今日,面前的男子并不是这样的。他从前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香颂,我不走好不好?”
爱情手段
那是两年前,香颂刚刚进入这间建筑设计室。推开白色木门,蓦然发现她的上司纪恩,正以微偻身形对住电脑,奋力地工作着。他不好看,但是他工作的样子像一头豹,非常有吸引力,香颂后来想到一个词,大概那就叫做性感。
那天他笑笑,要她坐,履行老板见新员工所要交谈的内容。然而话语之间,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也就此发生,根本措手不及。他复又投入忙碌中去,她走了。关门时见到他侧面四分之三的侧脸,有光洒在脸上,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文艺复兴。
她常常想他,一个上午,抬头十数次,有三分之二落空,三分之一,四目撞到一起,擦出咝啦啦的电火花,从他的玻璃间到她的格子间,一路上野火花窜烧成旖旎的星星。
再后来,他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只是对着香颂的格子间发呆。他是有股痴性的,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男人,香颂想,37岁,难道37岁以前的日子,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吗?她真的不明白。
到下午他工作积压,需要加班到深夜。香颂高跟鞋嗒嗒嗒走过,按电梯,下班,她才不管他,要他自作自受去。
纪恩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听见香颂格子间有手机的鸣声。
铮铮,铮铮。声音响了很久。他不好去接听,又被吵得头痛,没办法只好给香颂家里打电话,“香颂,你手机落在了办公室。”
那边却说:“你帮我带过来嘛。”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讲话,从没!他是一个严厉的上司,动辄吓得一干人等屁滚尿流。可是香颂却对他指手画脚,撒起了最荒唐的娇。她不怕他,因为她知道他对她的兴趣,她知道他被她吸引,玩于股掌,在劫难逃。
37岁,纪恩正处在人生美好黄金秋季,五谷丰登,万物成熟,经验加智慧,使他无往不利,可是他缺少那么一点绮思,人生都太正大光明,他需要那么一点不正,那么一点歪,那么一点趣味。而这些,27岁的香颂恰恰都可以给。
他果然送手机到香颂的公寓。“以后不要忘记了。”
她想,你可真是道貌岸然,还装!
“知道啦!”最后一个音拖得长长的,像柔软的绳索,将他一勒。他愣住了,看她正把手机在手里摇着,一脸精致的淘气。
如此深夜,是他自投罗网。她芳香的洗发水混以一点点FENDI琥珀的后味,简直销魂蚀骨。其实诱惑一个男人是很容易的,并不需要怎样的技巧与聪明,但是要一个男人爱你却很难,香颂知道,她是个幸运儿,她两样都可以手到擒来,她怎能不奋不顾身?
那晚结束后,在她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他一睡如死,石沉大海,她看着他熟睡的脸,忍不住去触碰他长长的睫毛。据说男人睫毛长,是多情的象征。可她爱这个多情的男人。
她没有告诉他,手机,是她故意放在办公室的。
做情人的悲哀
纪恩从此赖在香颂家不肯走,他在香颂的浴间洗澡,在香颂的饭桌吃饭,在香颂的阳台抽烟,他连牙膏都用香颂那一管。
“香颂,”他温柔肯定,当她是青瓷细玉,轻轻触她双肩,“我真喜欢你。”她知道在那一刻,他是真心喜欢她,没掺半点假。但是喜欢是什么?年三十的晚上,香颂有点迷惑,喜欢不过是一瞬间荷尔蒙错乱吧,就像一个拨错的电话号码。
香颂替纪恩倒一杯茶,茶在水里花一样绽放,转眼静止沉落,不动声色,水冷了。他一口没动,只是不停看表。香颂终于笑:“喝了这杯茶,你才可以走!”
做情人,最难过便是这样的节日。这样的日子,万家团圆,可是没她的份儿。她爱他,就得替他着想,万事不可穿帮,他要回去陪妻儿,逢场作戏也好,同床异梦也好,那戏得演,那床得同。
听到香颂松了口,纪恩如释重负。他不要喝茶,他站起身,讨好地说:“香颂,我过几天就来看你,我们一起去周庄……”
这话还没说完,那杯冻顶乌龙茶已尽数泼在他脸上,香颂拿着空茶杯转身,“不送了,纪先生,有时间再聚。”
多余的角色
乌黑缎衫,相当漂亮考究,特意在那两管袖子边缘,用挺薄的纱料绾结,手工压出明暗鱼鳍纹路。用张爱玲的话说是,“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
香颂觉得自己就是这件衫,黑得不见天日,黑得明珠暗投,黑得非常盲目,黑得十分浪费。
虽然,她也并不缺少一张暖怀,但终究,她扮演了一个多余而又凄凉的角色。
一个人的大年夜,香颂喝得半醉,CD里放着惨淡讽刺的音乐,她穿着新衣,自己跟自己跳舞。
那乌黑缎衫,泼上了红酒,天亮时已是一片盈凉。
年过完了,纪恩不食言,果然在安排周庄的事。香颂无可无不可地去了,也无可无不可地开心着。在船上,纪恩握住她的手,老老实实地说:“香颂,就这样一辈子多好。”
香颂忍不住要讽刺他:“你一天都不肯多给我,谈什么一辈子呢!”
他知道她是气他年三十不陪她,他便认真陪个不是:“香颂,对不起,香颂,这次我一定想办法,有个了断。”
乌篷船在水上慢慢地飘,天气很好,水由深灰转成碧绿。两个人一时无话,香颂只是把手伸到水里去,去捞那水面上凋残的荷花灯。纪恩忙拦住她:“当心着凉。”
他有时候是真好,好得不能再好,这般的细腻周到而又从无拂逆,会令女人甘愿爱他,甚至甘愿为他死。他有家?不,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她的错,这根本不能用对和错来说。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情公子空牵念。既然有这样的温柔牵念,也不枉她这辈子这一腔火热的情意了。
摊牌
话既然说定了,纪恩要好好做给香颂看,也要做给自己看。周末,他第一次摊牌失败,回到香颂的小公寓喝酒,口里一直叹气:“她不肯,孩子太小。”
香颂打开音乐,又是春节那几首调子,真不巧。“原谅你,和你的无名指,你让我相信还真有感情这回事……”
香颂看着这个男人,这不是一个狡猾的男人,其实挺憨厚,然而他太不聪明,她觉得他越来越小,小得像个孩子,在她怀抱里这般烦恼,怎么哄劝都无济于事。香颂也便烦了,丢开他,一个人下楼去逛逛。门外面,车水马龙,夜刚刚开始。她走着走着,发现纪恩也跟来了。于是两个人在西餐厅点了一份牛排,分着吃。
吃着吃着,他忽然呆住了。他发呆的样子其实是很好看的,就像第一次见到香颂,从那白色木门里面,用那大大的眼睛,那样惊艳地望她。
香颂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他回过神来,低声对香颂说:“那个。”
香颂回头看去,见到远处一个小妈妈正在喂孩子吃饭。女子神态温柔,几乎让人肃然起敬。小孩,非常可爱,像毛茸茸的小熊。
他惭愧低头,带着香颂快速逃走。
暧昧的身份
在街头他慢慢地说:“香颂,活着真麻烦。”
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天良未泯,为了道德这事儿拼命挣扎,一年间他已经老了很多。
他拉香颂的手,他手大而厚,“香颂,我再去试,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他的承诺说得艰难,因为他的心思下得太重。香颂把这手贴在脸上,不忍松开。喝了酒,人有点神经质,她笑,忽然甩开他,穿过人群和马路,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小货车没能及时刹住——
急诊室里,香颂头缠厚厚的纱布,终于醒了过来。纪恩把脸凑得很近,眼泪沤着,眼睛就红了:“香颂,你没事吧,香颂?”
他是这样的好,他这样为她焦急,已经抵得上她对他全部的爱慕了吧。香颂皱皱眉,声音平静冷漠:“先生,你是谁?”
“香颂,你怎么了?”
“你是谁?”
“香颂,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纪恩啊。”
“可是,纪恩是谁?”
他哑口无言了,他说不出来“纪恩是你的情人”这七个大字。
他见得光的身份只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一个小孩的父亲。
“我是你的上司!”他急了,竟然来了这么一句。
所谓的情爱
两个月后,香颂头上伤口愈合,纪恩开车来接,而她拒绝了这位“陌生人”的帮助。“你到底是谁,干吗总来骚扰我?”香颂的选择性失忆症,表演得天衣无缝,非常的完美。
然而,这却是一个充满了悲伤的阴谋。
香颂叫了出租车扬长而去。回到家,把公寓的门锁上。
她开始流眼泪,却又觉得放松和幸福,她想,他从此不会再烦恼了吧,他从此可以兢兢业业和他的妻儿生活,没有绯闻,没有艳屑,他会坦荡荡,光滑宁静地过完他的一生。
不会再说“真烦”,不会再皱眉头。不必再担心她的任性,不必再怕她着凉。
其实所谓情爱,有时候不过是一场悲悯的游戏。
弃暗投明
辞职后,香颂偶尔还是会遇到纪恩。
他试图对她微笑,看她有什么反应、可还记得他、会不会忽然认出他。
渐渐发现,没有用。
他于是放弃了。有一次,他带着妻子,抱着孩子,在游乐场玩耍。香颂也正和新男友在里面晃荡。
彼此路遇,香颂心中一紧,汗就微微染上了手心。忽然又想,没什么,她不早已是一个失忆症患者了吗?
而这次,他没有再对她微笑,当做一个路人一样走过去了,头也没回。
看来,他已经病愈,自那场令人窒息的情爱里,抽丝般好转。
他瘦了。
香颂叹口气,垂下沉重的睫毛。多情公子空牵念,却休怪我,无情无义。香颂此后不再穿黑,现在她穿一身珍珠白,戴银色太阳眼镜。她渴望有一次热烈坦荡的情爱,好过黑色的不见光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