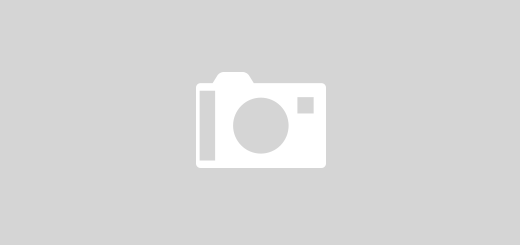光怪陆离的上海每天上演着爱的游戏(1)
1999年,我是一名物业经理,管理一批上海老式花园洋房改造而成的公寓,那里有宽大的草坪和市中心少见的古树。那里的房子有着最古朴的外貌和最时尚的内部装修,每月的租金在6万人民币以上,里面的租客非富即贵。大概地址?恕我不能透露太多。嘿嘿。
两年的工作时间里,我看着一群金领老外们搬进搬出,伴随这些的,是那些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或英语的女人们的搬进搬出……
一号楼的故事
(一)第一号的住户:台湾小姐-猫
我们背后叫她猫,是因为她养了只黑猫,她是所有租客里唯一养宠物的。
猫小姐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家里陈设的一把绣迹斑斑的剑,据她有一次透露,是蒋**当年赠送给他爷爷的。
当年做为愤青的我,每天下午检查阿姨HOUSEKEEPING,经过那把剑的时候,都要呸一声以示轻蔑。
猫小姐的男人,是个不苟言笑的德国人,执着于每天的晨练,(有天早上上海下着大雨,他穿着晨练服从物业办公室窗前跑过。由此印象特别的深刻),台湾小姐会做很多菜,我想她深谙一个道理: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德国胃也不例外)。
台湾小姐长的确实不好恭维,但是菜却做的很香,德国老外几乎每天都会按时下班回家吃饭。猫小姐除了出去SHOPPING就是在家研究菜谱。他们在花园里一共住了两年,猫小姐的手上却始终没有戴上戒指。
(二)台湾小姐搬走后,租下她房子的是:美国玫瑰
美国玫瑰其实应该叫美国公主,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在美国领馆工作,并且租这么贵的房子,每天接送她的车是劳斯来斯,司机拒绝和我们的保安聊她的任何情况,我们肯定她的来历不简单。
玫瑰美的十分娇嫩,但是没有一点傲气,和你说话会脸红,眼里还闪着点泪光的样子。
玫瑰是花园里所有清洁阿姨的天使,她有时候日常用品没有了,会给我留个便条,大意是桌上有100元钱,请阿姨给我买包(洗衣粉,柔软剂之类的),剩下的找头阿姨不用还给我了。逢年过节也会给我留个便条:桌上有些红包请分给阿姨和保安(每个红包都是100元)。
玫瑰从来不投诉阿姨清洁工作不干净之类的,每天进出都会很温柔的对保安或阿姨说声HI,所以,玫瑰差不多是所有人心中的天使。
直到有一天,保安很失落的告诉我,玫瑰开始带男人回来了。而且,经常是不同的男人。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也许国外的女孩子都这么开放吧,后来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玫瑰搬走的那天,所有的保安都出来帮她搬行李,清洁阿姨眼泪汪汪的,玫瑰和保安头老李握了手,老李那天失了魂,不停的和每一个他见到的人说:玫瑰的手,雪嫩啊。
(三)玫瑰的楼上住的是洋葱夫妻
洋葱夫妻是德国人,因为脸都是红红的,所以我们叫洋葱夫妻。
洋葱们搬进来时却并不是夫妻。
那时候我才知道,在上海想傍个有钱老外的并不全是亚洲女人,其实很多女老外在上海漂的目的也是为了找个有钱老公。
女洋葱在一家小洋行工作,薪水低也没什么地位,男洋葱确是世界有名的大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女洋葱把男洋葱看的很紧又很宝贝。时刻注意男洋葱有没有和谁勾三搭四(男洋葱司机的话)。
女洋葱真是个素质不高的外国女人。
她一旦在家里发现什么问题从来不打电话直接在阳台上大呼小叫:AMANDA。
有一次阿姨把她颜色鲜艳的衣服和白衣服混在一起洗,结果白衣服染了色。她瞪着铜铃眼都快能吃了我。我赶紧代阿姨道歉并提出赔偿,她很嚣张的说:300多美金,你们阿姨赔的起吗?
后来阿姨提出每天帮她额外做些服务作为补偿,她答应了,结果阿姨的噩梦开始了。
从一开始增加打蜡到后来全部衣服都要手,最后到了要帮她种些葱以备不时之需的琐碎程度,半年后阿姨被迫辞职了。
因为之前没结婚,飞扬跋扈的女洋葱对男洋葱是很唯唯诺诺的。
但是半年后洋葱运气来了!(洋葱运气来了绝对是有预兆的,她阳台上的铁树开花了。每家都有铁树一盆放在阳台,唯独她的在那个闷热的天气里,开出了一朵花)她喜气洋洋的宣布:她怀孕了!
两个月后,花园传遍了了洋葱要结婚的喜讯(奉子成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啊)。
洋葱趾高气昂的戴着烁大的钻戒和我在大门口拉家常,询问我中国特有的结婚的黄道吉日怎么计算的,洋葱高昂的声音也显得分外刺耳。
她跟我抱怨厨房有蚂蚁,我进去看的时候,看见她挺着不明显的肚子,很拽的用中文在和保姆(男洋葱在她怀孕后额外雇的)说:萧红(小红),你不可以呲呲呲(指用杀虫药水喷),你应该乓乓乓(指用手去拍蚂蚁)。
女洋葱和男洋葱说话的语气也完全不一样了,男洋葱甚至没了在家抽烟的自由,于是男洋葱每天从家里出来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公事包放在大厅,然后点上一支烟。
女洋葱是花园里唯一结成正果的靠的是年近40的一个男人对骨肉情感的回归……
(四)孤独的雄太郎
洋葱的楼上,住着一个单身的日本男人。
小时候看过的一个日本卡通片,里面有个雄太郎,我就一直叫他雄太郎。
雄太郎是一家日本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如果他不说日语,看上去就象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
在我之前,花园原本有个物业经理,一个小姑娘,结婚后辞职了,雄太郎以为是我把她挤走的,对我很是愤怒,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和我说话,后来从保安那里知道实际情况后,对我大概很抱歉吧,所以每次看到我都是笑嘻嘻的,我本来是非常讨厌日本人的,这下子倒对他有些好感了,觉得他也算是个很锄强扶弱的人。
一个春天的下午,雄太郎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让我帮他找个拉二胡的老师,我也没多想,就随便在网上给他找了一个音乐学院的女学生。
椐保安说,从雄太郎买回二胡的那天开始,花园周末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雄太郎拉锯似的二胡声让楼下的*国玫瑰和洋葱夫妻恨到了极点,尤其是洋葱,拉长了一张脸,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叽里呱啦的来物业投诉。
投诉了大概两周后,我正头疼怎么解决呢,突然,保安汇报说雄太郎不学了。
我忍不住去问雄太郎为什么不学了。他说原来的老师出国了,介绍了另一个,他就不想学了。我说为什么呢?他的小甜瓜脸红了一下说:因为那个新来的是男的!
雄太郎不拉二胡了,紧接着外出旅游了半个月,回来给我带了串贝壳项链。
再过了两三个月的样子,从不带女生回来的,洁身自好几乎是花园楷模的雄太郎,居然带了个女生回家!而且还是过夜的!保安一大早等我来上班就迫不及待的告诉我了。绘声绘色的。
椐保安回忆,是个年纪很轻的,很腼腆的上海女孩子。
雄太郎在第二天,曾对着保安小安,很严肃很幸福的说:我是要和她结婚的!(雄太郎的中文在花园里的老外中算很不错的,和保安拉家常是他的一个爱好)。
小女生住了大概两个月后,某一个周日的下午,雄太郎突然没头没脑的跟保安头子老李说:和中国女孩结婚,好象很麻烦……
再后来,小女生就慢慢不来住了。她大概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相信男人在和你上床前说的任何承诺。
寂寞的雄太郎,偶尔在周日的下午,重新开始拉一首支离破碎的二泉印月。
二号楼的故事
(一)红色公主
二号楼的第一家是个中国女人,大概30–40岁的年龄,很清秀,很冷漠,很威严,这是花园里的人对她的评价。
这个单身的中国女人,住着二号楼最贵的那套房子,有必恭必敬的司机每天开着宝马接送。
司机来送的第一天,保安头子老李就和他混熟了(老李一直觉得以自己保安头头的身份,和住户的司机秘书们应该是平起平做的)。帮中国女人搬完行李,老李神秘的跟我说:侬晓的伊是撒拧乏?红色公主!”看我还木知木觉的,老李和我解释了什么叫红色公主。
红色公主有个很有特色的名字,我想大概只有革命老一辈才会给自己的孙女起这样的名字吧。
公主在一家外资企业担当的是高管的角色,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来拜访,周末就在家看书画画,画的一手好油画。阿姨则在旁边给她炖各种各样的广东汤。公主家是唯一能在美食上有资格有能力与台湾猫小姐抗衡的。(其他老外在伙食上几乎没有什么优势,用老李的话来概括,塞古啊,切的来象猴子)
搬进花园后大概8个月,春天的一个下午,公主提前下班回来了。公主苍白的脸上有少女才有的红晕。公主对老李说,今天有客人会来找我,你到时候带他进来。
公主的声音很轻很好听,这是我和老李第一次看到公主这么幸福的样子,于是,我们比她更兴奋的等待着。(八卦的资质要靠长期的培养)
公主等来的,是个30–40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很简洁的T恤和棉的长裤。简单的行李,开着一部我叫不出来的车,很简单的一个人,却有着震慑人的感觉。他客气的和我们打过招呼后直接进了花园,平时话很多的老李楞了很长一会。我的直觉告诉我—红色太子!(这一点立刻在第二天老李和公主司机的抽烟碰头会上得到了证实)
太子住了半个月,椐老李和阿姨交头接耳的结果,太子和公主是止乎礼的。
公主的幸福显而易见的洋溢在脸上,她没法再按时上下班,她陪着他逛遍了整个上海,阳光灿烂的周末的下午,他们坐在花园的草坪上,她那样抬头看着他,满足的微笑着。谁都能看出来,她是这样的爱着他!然而,一个许文强似的他,始终微笑着,淡淡的看着周围的风景,却看不到旁边那个期待的她。
太子半个月后离开了。后来每年都会来住半个月。那半个月,是公主的春天。
(二)中国公主的楼上,住着的是鸦片夫妻
和洋葱夫妻一样,鸦片夫妻并不是夫妻。
鸦片是个新加坡女人,她的客厅里摆着一张清朝人吸鸦片的鸦片床,雕龙刻凤的。她拿它当沙发用。每次去找她都看见她躺在上面看电视或报纸。所以我们索性称她鸦片了。
鸦片的男人是个一丝笑容也没有的新加坡人。住了两年,我都没注意他叫什么名字。
鸦片和洋葱一样,在花园属于人见人烦的,投诉是她的最爱。几乎每周都有事情要来投诉。有一次她投诉花园水管有问题,水发黄。我被迫在她的厨房里呆了两个多小时,她和她的阿姨用白瓷碗装满自来水和农夫山泉的水来做对比,给我看了一次又一次。我解释上海水质基本就是这样,但是她坚决不接受,我们俩的英语对白从斟词酌句到提高分贝。后来几乎彼此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了,只能比谁的脸更红,脖子更粗。
鸦片无法改变花园的水管,更无法改变上海的水质,但是鸦片可以改变自己的阿姨!从此鸦片洗头的时候,她的阿姨就站在旁边,高高的举着一大桶农夫山泉,缓缓的浇下去。
这个勤勤恳恳的阿姨,是很值得在此写一笔的。她是鸦片他们自己雇的,就住在鸦片的家里,鸦片的男人每天早上6点就要出发去上海的某个郊县工作。阿姨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给他做一顿热乎乎的早饭。看着他出门了再去睡了回笼觉。鸦片曾经跟阿姨说,不用做早饭,让男人自己去外面买点什么随便吃吃。阿姨说不行的,先生很辛苦,早饭要吃的好一点。据新加坡男人的司机后来跟老李透露,男人曾经感慨的说,最心疼自己的人其实是阿姨。
老李对此也曾经屡次发表感慨:男拧么,早饭侬都乏帮伊烧好,还要讨侬做老婆作啥,啊拉女拧……(此处省略若干家庭细节)
就老李的观点来看,鸦片的始终未转正,和她的不知嘘寒问暖绝对有很大的关联。
鸦片在花园的两年生活里琐碎而平淡,唯一起过一些波澜的,是红色公主内衣事件。
鸦片有阿姨,红色公主当然也有自己的阿姨。鸦片的阿姨心疼的是男主人,而公主的阿姨心疼的是公主。
话说某一个周六的早晨,公主加班去了,公主的阿姨在一楼的小庭院内晾晒公主的衣服,其中就有公主的某些蕾丝BRA和KK。其实公主曾经跟阿姨提过内衣晾在浴室,千万不要晾在外面,但是阿姨没听从。据阿姨后来挤眉弄眼的解释,她觉得女人的内衣应该多晒,否则容易……(此处省略若干年老妇人的生活经验)
时机凑巧的是,二楼的新加坡男人当时吃好早饭,因为不用上班,在厨房窗口望出去,正欣赏园中美景。突然就看到了公主美丽的蕾丝小衣服。此后根据二楼阿姨激烈的辩驳,我们相信他当时目光立刻掉转开了且看的是公主的庭院盆景。但是发现了异常情况的鸦片却当场发了彪。与自己老公大吵一场后,余怒难消的她冲到物业,从老李那要来了公主的办公室电话,当场拨了过去。(当时我因为是周末所以不在办公室)
两天后的周一的早上,心有余悸的老李给我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以鸦片后来的语调语气分析来看,电话线那一头的公主措辞并不友好。鸦片没接收到她希望接收的类似道歉之类的信息,气咻咻的冲回了家。
鸦片的脸板了一个月,进出大门也不再和我们打招呼,她威胁说要搬走,几乎一天一个电话的催我早点找到新客户好让她退租。
然而在一个美国客户看中她的房子,并要求立刻入住后,鸦片突然又不愿意搬了,甚至在接下来的中秋送了我们每人一盒月饼以示友好。进出大门的时候也会挤出一些笑容来和我们说HI。
鸦片最终在两年后搬了出去,因为新加坡男人回国了,她后来去了哪里,就没人知道了。
三号楼的故事
(一)三号楼的第一家,住着忧郁的男人巧克力
巧克力是新加坡人,公司的产品中有好吃的巧克力,他入住的第一天,我和老李就吃到了他的巧克力,从那一刻起,表面上他还是Mr**,背后他就成了巧克力。
巧克力人也很巧克力,黑黑的很结实,大概50岁的样子。他的母亲是上海人,很小的时候远度重洋去的新加坡。今年已经80多岁了,所以当巧克力看到老李卖力的帮他提箱子时,就流利的说了句:谢谢侬。老李一激动差点去摸香烟走他熟悉的司机路线了。
巧克力搬家找的是外国人开的搬家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上海工人打包再拆包,再一一按照他的要求去摆放好。第一次看到这么正规的搬家公司,显然我要留下来瞧瞧热闹。
拆包工作快结束的时候,工人们显得很累,手脚都开始有些重了,(巧克力的家伙真不少,连垃圾桶,报纸架都有,这是有洁癖的男人),然后在拆到一个很小的箱子的时候,突然听到叭的一声脆响,大家都围了过去一看,里面是个有年头的瓷碗,断了只小耳朵。巧克力捧着小碗象孩子一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鼓着嘴轻轻的说:坏掉了。工人的脸刷拉丝白,带着哭腔说:要赔多少钱啊?巧克力一脸的痛惜,轻轻的说算了算了。
搬家风波平息之后,巧克力接下来就开始了他在花园的安静生活,每天早上8点离开,每天晚上8点回来。住了半年没有一点波澜可以让人议论。这着实让老李和阿姨们感到无趣。
好在老李是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无趣变有趣的人,当梅雨季节来临,绵绵不断的春雨把老李留在了物业办公室无处可去的时候,老李就开始在我耳朵旁边叨咕着,说巧克力和红色公主看上去如何如何般配(帮花园里的孤男寡女配对,常常是保安和阿姨们午饭时间的热门话题),如果傍晚时分进花园的时候大家能遇到且两目相对,或者周末在草坪看书的公主突然看到自己在给客厅给地板打蜡的勤劳的巧克力。再或者雨季喜欢在花园散步的公主让临窗眺望的巧克力砰然心动并送上雨伞,那么接下来等等等等。
大概因为老李叨咕的太多太琐碎,其中又搀杂了太多了上海俚语,结果仁慈的上帝没听清楚,虽然出手让巧克力和公主是有了一次接触,却全然不是老李希望的那样……
无处不在的上帝在巡视了一番花园之后,最终决定让公主与巧克力相遇的契机停留在一个我新买的花园秋千上。
说起那只秋千,由不得我要骄傲一下。那只白色铸铁带有绿色顶棚的秋千是我花了两百块从旁边一家花园洋房里买来的二手货。虽然是二手的淘汰货。可放在花园宽大的草坪上真是太漂亮了。玫瑰、洋葱、小章和鸦片成了常客,美女们坐在秋千上看书,也就成了花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样的风景看的多了,轻易不露面的公主也被打动,于是在某个周六的早晨大概9点左右(为什么坏事总发生在我不上班的周末?老李常称赞我是镇园之宝),公主来到物业,提出要把秋千搬到花园中一棵茂盛的梧桐树下,她想坐在那里看会书画会画。
当班的小安二话不说,当场就把好人好事给做了。
公主在梧桐树下荡起了秋千,美丽的画面我现在是无法呈现给大家了,但我最想呈现的,却是我们花园的地形图。亲爱的铜子们啊,这棵梧桐,它,偏偏就种在三号楼一楼的巧克力的卧室前不超过5步!
而我们亲爱的忧郁的巧克力,他的周末懒觉在花园物业处是众所周知的,清洁工阿姨在周末进去做HOUSEKEEPING都是在下午两点后才敲门的。
那天,我们亲爱的巧克力就在甜睡中被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给弄醒了,睡眼惺忪的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就看到一个女人荡秋千的背影伴随着折磨人的吱呀声。(如果看到的是公主的脸,也许结局就如老李所愿了?)
巧克力作为一个有涵养的人,他没有当场发作。在忍受了一个早上的骚扰,公主起身离去后,巧克力来到物业,坚决要求把那只秋千放回原处。
小安二话没说,又把好事给做了。
巧克力没有错,公主也没有错,有错的是小安。他没有把这件事记录在物业交班笔记上。
于是,第二天早上,当公主再次来到秋千前,发现秋千神奇的回到了草坪中央,并曝晒在太阳下时,公主不得不再次来物业求助。
当班的老李象吃了仙丹,脸不红气不喘的,轻飘飘的就把秋千又给端到了梧桐树下。
于是……
这次被吵醒的巧克力,再也没了好脾气。他刷的拉开窗帘,对着公主的背影说LADY,YOUBOTHEREDME(小姐,你吵到我了)
公主吓的摔在了地上,巧克力也闹了个红脸,听到声音跑出来看的老李更是吓傻了眼。
孤家寡人的巧克力和行单影孤的公主,也许他们原本在这个花园里真的会有这么一段佳话,可惜却终结在了小安、老李,我和这个二手秋千上。
(二)对不起我爱你
巧克力的楼上,住着一个瑞典男人
瑞典男人供职的公司做的是电器,瑞典男人也象电器,外型美好,人却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气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男人的帅,某些角度看起来很是象布拉德-皮特。
瑞典男人进出花园从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用阿姨的话来说象只幽灵一样
幽灵一般的瑞典男人身边有个女人,一个抽摩尔烟的上海女人。
摩尔是那种外表很野性的女人,皮肤晒成小麦色,画着咖啡色的眼影。栗色的微卷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
摩尔和小章一样早上上班也很晚,每天差不多10点了才看着她背着很大的背包,急匆匆的赶出去。但摩尔和小章不同的是,她从来不和我们打招呼或笑上一笑。
摩尔和电器没有自己的阿姨和司机,从老李他们零星打听来的信息综合分析,只知道她和电器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电器是GM,摩尔是部门经理。
摩尔和电器初期是很如胶似漆的,有时候他们下班回来走在微明的花园里的小路上,电器搂着摩尔的肩膀轻声悄语(摩尔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常常会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那时候他们两人看上去,就象一对平常的恩爱夫妻。
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英俊的”电器”开始有了变化。
在摩尔偶尔回自己家住一两天的时候,电器偶尔会带一些很妖艳的看上去象在酒吧里混的女人回家。然后会有超市的人送成箱的啤酒进去。再然后房间里会传出震耳的音乐和女人夸张的笑声。
摩尔是个聪明的女人,时间久了也许是她发现了什么,于是有一天,摩尔和电器发生了一场争吵,那天他们都没去上班,清洁阿姨来报告说在二楼的楼梯上都能隐隐约约的听到他们的争吵声。临近中午的时候,摩尔拖着一个皮箱离开了花园,摩尔没有哭,但是连老李都说,摩尔看上去很伤心……
摩尔的离开,对”电器”是有影响的。至少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电器晚上回花园的时候不再带乱七八糟的女人回来了。
但是一个月之后,摩尔依然没有搬回来,电器就恢复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这苦了住在楼下喜欢清净的巧克力。常常在晚上11、2点的时候打电话来保安室,投诉电器的音乐开的太响,让他没法睡觉。
同样无法入睡的还有威廉王子,他投诉的则是鸦片家的空调外机。
而鸦片投诉的是花园的水质。
虽然琐碎的烦恼充盈着整个花园,然而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进行着。99年的上海,初夏过去的很快,当花园里花匠新种的爬山虎绿了整个洋房外墙的时候,我接到了”电器”公司财务小姐的电话。
财务小姐直截了当的向我提出了退租,并爽快的答应了赔偿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协商完退租事宜,我顺便问财务小姐,为什么”电器”要退租。财务小姐笑的象银玲一般:”阿拉公司勿要伊了,伊么只好回去了”
就在电器打包整理完东西,叫我去房间内清点的时候,我突然在电器的身边看到了久违的摩尔。
神情淡漠的摩尔还是没有和我打什么招呼,她细心的帮电器整理着厨房里一些零碎的东西,轻声轻气的问他这个是不是留下,那个还要不要装在包裹里。电器回答她的声音也十分温柔,倚在墙壁上看着她整理,有时候会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而她则回抬起头来,对着他微笑。那一瞬间,我想起了他们搬进来时候的情景,轻声细语的,走在花园的小路上,象极了一对恩爱的夫妻。
东西清点完了,行李都搬到出租车上的时候,摩尔站在花园大门口,仰起头来看着电器说我送你去机场,好不好?电器很温柔的说不。摩尔说好。
摩尔微笑着看着电器,电器也微笑着看着摩尔。
夏天的傍晚,凉爽的风里有着金银花的香气,两个曾经相爱的人,站在1936年的老房子前,看着彼此最后的影像。
(三)漂泊的蕾丝
电器的楼上,是和威廉王子的住所一模一样的昂贵的复式房。住着一个很年轻的法国人和一个很憔悴的中国女人。
年轻的法国人是AT一家规模庞大的汽车产品制造公司的GM。非常可爱的一个年轻人,高而瘦,顶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对花园里每个人都很客气。和”电器”的冷漠不一样,汽车每次看见我们,都要很阳光灿烂的挥挥手说声HELLO,在花园住了两年,我从没见过他不高兴的样子。
汽车的身边依偎着一个非常憔悴非常瘦弱的中国女生。喜欢穿暗色调的衣服,看到我们只是很羞涩的微笑,异常的沉默。搬进来大概一个月以后,她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请个阿姨,我推荐了一个上海阿姨长脚给她。
长脚的家务活和八卦能力是成正比的,仅用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中国女生的所有的故事,包括她喜欢带蕾丝花边的雪白的床单。
蕾丝的家乡在遥远的甘肃,家境很贫寒。蕾丝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外国语学院的法文系。毕业后去了大庆附近一家汽车产品公司,做着办公室文员的工作。
举目无亲的蕾丝,在别人的撮合下嫁给了当地一个男人,但是婚后蕾丝才发现这个男人有家庭暴力,瘦弱的蕾丝常常被打的鼻青脸肿。
1998年,”汽车”去了蕾丝所在的工厂参观,蕾丝的法文功底让她成为了汽车的临时翻译。
蕾丝告诉长脚,见到”汽车”的第一瞬间,她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是微笑,她觉得”汽车”就象是她上辈子的爱人,今生在此重逢。而”汽车”也温柔的看着并不美丽的蕾丝。在熙熙攘攘的办公室里,当地记者不停拍摄的闪光灯中,蕾丝和”汽车”沉默的互相凝望着。
在汽车即将离开大庆的时候,汽车问蕾丝,你愿意和我去上海吗?
从男人吻你的部位看他的品质如胶似漆明星情侣们的罕见恩爱照片
汽车坚持在大庆又停留了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蕾丝办完了所有的离婚手续,和汽车来到上海。
长脚问蕾丝,你老公肯轻易和你离婚吗?他没打你啊?蕾丝把脸转了过去,沉默了。
长脚在和我们说的时候红了眼圈,长脚自己有个20几岁的女儿,宝贝的象珍珠一样。长脚说,以后谁敢打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了。
蕾丝的身体似乎一直复原,她没有上班,静静的住在花园里,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安静的走出去吃午饭,回来的时候手里总是拿一枝红玫瑰。
而汽车对蕾丝的感情,更是让人惊诧。
蕾丝喜欢住老式花园洋房,但这就意味着每天早上4点半汽车就要出发,赶去公司上班。(汽车曾经以管理严格而上过电视,他自己更是从来不迟到)。但是只是因为蕾丝,汽车就无怨无悔的每天这么奔波着。
汽车几乎每天都是6点准时回到花园,然后给蕾丝做饭。长脚说汽车做来做去就是三明治或者乱七八糟的面条,但是蕾丝吃的很开心。
有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蕾丝和汽车在花园里散步,汽车突然背起蕾丝,在花园里奔跑起来,老李说,汽车笑的象孩子一样,虽然看到老李和其他老外都在哈哈大笑的看着,汽车还是一圈圈在跑,蕾丝满脸通红的拍着汽车的背,汽车绕着花园跑了几圈才把蕾丝放下来。
当时花园里的老外都鼓着掌吹着口哨,像极了大学校园的爱情……
可是蕾丝依然是注定漂泊的。
汽车在法国,还有一个等待他回去的妻子。
长脚曾经问蕾丝,会不会要求汽车离婚或着跟汽车去法国。蕾丝转过脸去看着厨房窗外,很平静的说,我不会。
汽车的房间里有两个电话号码,我们有事情通知蕾丝,只打其中的一个号码,我们曾经尝试另一个号码,她一直不接。也许那个号码,是留给那个等待丈夫归来的法国女人吧。
蕾丝的一生,拥有一份绚烂的爱情,却短暂一如她手里的那枝玫瑰。
四号楼的故事
(一)等待的荞麦
四号楼的第一家,住着健硕的石油和美艳的荞麦。
石油是个30多岁的美国小青年,在中国过着年薪百万的好日子,但是在美国老家佛吉尼亚却是吃着苦头长大的。
石油有一个常年失业的酗酒的老爹,养了大大小小6个孩子,石油在家里算是顶顶有出息的,硬是靠着刷盘子扫花园读完了大学,学的是热门的石油天然气方面的专业。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天然气公司做了几年,然后被外派到上海公司。
来到上海的石油,很快就发现,在上海的他,除了有比在美国更丰厚的薪水外,还获得了无数结婚的机会。
上海贸名南路那些彻夜狂欢的酒吧,促成了无数的奇遇,包括我们的石油与德国美女荞麦的狭路相逢。
荞麦和洋葱,这些异国的家境普通的女孩子,匆匆忙忙的读完大学,就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绚烂的梦想,来到上海,寻找工作,或是结婚的机会。
荞麦在静安寺和另一个外国女孩合租着一套2500块的两室户的房子,家具是东拼西凑毫无品位可言的。睡到下午三四点起床,仔细画完妆,再冷的天脱掉大衣也只剩一件薄薄的露出胳膊的紧身毛衣。眼皮上闪着金色咖啡色或银色的亮粉,买一杯最便宜的啤酒或根本什么也不买,专拣那些女士免费的酒吧,和任何有眼神接触的男人答腔,也许只是ONENIGHTSTAND,也许就有了成为MRS**的机会。
在上海漂了近十年,真真假假的无数艳遇之后,荞麦终于遇到了贵人石油,没多久,就从静安寺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月租7万多的花园。
荞麦的日子宽松了,人也越发显得滋润了。刚进花园的时候瘦的秸杆一样,长长的腿从超短裙下面伸出来,刀削木棍一般。然而到了后来,荞麦穿着紧身的连衣裙,上面画着牵丝攀滕的暗紫带金的花纹,丰满的紧张曲折,胸口一片雪肤。
荞麦慢慢能讲一些语法地道的英语了,带点佛吉尼亚的口音,她吐气如兰似的来跟我抱怨,说是家里有隐约的煤气味道,偏遇着石油不在家,让她一晚上不能入睡。
荞麦抱怨归抱怨,却不需要上门查看,只是让你知道她虽然是住惯了2000多的房子,但是对70000多的房子还是有着很多不满。
好在日子久了,荞麦和洋葱搭上话成了朋友,常常聚在家里烘陪些点心什么的。也就不大来物业说这说那了。
然而阿姨开始在物业说荞麦了。
阿姨的诉说常常是耳语的方式,可是事情还是描述的请清楚楚的。
大意就是荞麦太热情似火了。
荞麦的热情在搬进来的当天就露出端倪,别的行李尚未整理的时候,荞麦就先在客厅,浴室和卧房分别挂上了三张照片,不着寸缕,玲珑有致。搬家的民工们红着脸,阿姨们背过去笑的格格的。
荞麦却全然不在意,周末的下午,在花园的草坪上扔块垫子,穿着省到不能再省的比基尼,栗色的身体小心的抹过防晒油,趴在那里作太阳浴。从下午1点一直到4点,似睡非睡的,慵懒的神态分外娇媚。
且不论周围居民楼里伸出的那一排啧啧做声的脑袋,就是花园里的男性住户,也常常被太太们从窗口领回去。
石油和荞麦的夜晚也是相当火爆的。早上阿姨去做清洁,回来总要和老李他们详细描述一番。什么荞麦和石油的衣服从客厅一直扔到卧室啦,荞麦的红色的KK在沙发,BRA却在浴室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既然已经把石油拿捏的十分稳当,听到洋葱要奉子成婚,荞麦也开始有意无意颇有些娇羞的跟我说:DAVID说是要求婚了,可把我吓着了”。我满脸笑容的恭喜恭喜,心里感慨着年近30的荞麦,如此这般的娇艳,顺利成章的应该把这样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然而直到洋葱热闹的婚礼结束差不多有小半年了,荞麦那里却始终没有再传来任何变化。
有了变化的是荞麦的花园好友洋葱。
洋葱很明显的和荞麦疏远了,在花园门口遇上,洋葱只是拉长个脸淡淡的说声HI,把原本要挽着她叽里咕噜说上半天的荞麦楞在那里。洋葱开始热衷于办一些太太聚会了,受邀的都是些有名有份的太太们,在洋葱看来,她无论如何属于”从良”了的,和荞麦之流绝对是有了天壤之别。
石油虽然还是和荞麦没心没肺的厮混着,却恢复了周末一个人去茂名南路那些彻夜不眠的酒吧的习惯,凌晨四、五点才醉醺醺的把保安叫醒了开大门。
荞麦渐渐换了种打扮,以前那些露着胸的衣服都收了起来,开始穿着正式的套裙进进出出,据说是在面试,想给自己胡乱混个差事,时间久了,又迟迟没有消息,荞麦不免焦躁了起来,出去的时候,套裙还是穿着的,许是放了太久或是压根没熨过,一道道的压痕。忖的人更加的邋遢。
洋葱分娩前突然搬了出去,说是要去朋友们多的地方住,顺便讨讨育儿经。忙着洋葱搬家的事情,也就许久没留意到荞麦了。再看见她的时候,觉得过了30的荞麦怎么一下子就老了。金黄的头发胡乱的用发圈圈着。以前密密的睫毛下象笼着雾一般的灰色眼珠失去了光彩,跟人搭话的时候一脸紧张的神色,难得笑一笑,嘴角眼角都是细纹。
到了周末,石油不见人影的时候,荞麦常常一个人坐在天井里的长椅上,腿上搭着本书,眼睛却楞楞的盯着镂空花墙在看,一直坐到保安把花园里的路灯一盏盏开起来。才百无聊赖的去把厨房灯打开,给自己煮上一碗面。
石油厌倦了老上海花园洋房的风情。租期一满就搬了出去,乔迁到了南京西路上的一栋现代化装修风格的公寓里。
荞麦的传奇也就没有了结局。
(二)人人都爱古太太
古太太,早。
古太太,今天要不要去买菜呀?现在的小青菜又糯又好吃哦。
台湾来的古太太是花园里最受欢迎的太太,每天早上出门,阿姨和老李都会抢着和她打招呼,古太太慈眉善目的,见人就带三分笑,看见老李他们吃午饭都会凑上去看看菜式,顺便讨论一下海派家常菜的做法。
古太太的先生是花园里最暴躁的人,矮胖的法国老头子,红通通的脸上缠着银须,虽然只有一米65,却应了那句老话,矮脚鸡往往是鸡群里最善斗的。
虽然古太太其实并不姓古,可是她夫君的法国姓氏又长又难记,而且又收集了满屋子的古董,叫她古太太也算是实质名归了。
古太太搬进来的当天,可让我们长了见识,那据说有一百年的磨盘,那据说是清末从宫里漏出来的古画,还有那据说是康熙年间的玉碗,林林总总,把个200平方的屋子堆的满满当当,最后,古太太又小心翼翼的从箱子里取出来了一把竹椅。
说起那把竹椅,怎不叫我棰胸顿足,这种竹子编的小椅子,靠背上刻着自力更生四个字,可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么,8几年的时候,嫌破当垃圾扔了。十几年后古太太在法国出了八百法郎,死活从法国友人那里挖了来,成了心头好,飘洋过海的又给带回中国来。
痴迷收集古董的古太太因为和蔼可亲,一进花园就受到众人的拥戴。可是转过脸来面对古先生,古太太可就脾气大了,即便古先生是在大公司做着总经理,在法国有着古堡的。傍晚出去吃个饭,等在大门口的古太太都会对慢腾腾的古先生一顿咆哮,直到矮胖的古先生气喘吁吁的从花园尽头跑过来。
花园隔壁的那家外贸服装公司,一到换季总有打折的衣服摆在大厅里卖,中午的时候大厅被白领们挤的满满当当的,都在那里找自己的尺寸,那天,满头大汗的我居然在拥挤的人潮中看到了古先生和古太太的身影。古太太眼神犀利的在那里翻着,从公司被叫回来的古先生孩子似的贴在太太身边,惊恐的看着汹涌的人潮,试穿着一件又一件古太太翻出来的西装。那场景着实让人觉得滑稽。
对此,老李的看法是:夫妻么,一块馒头一块糕,搭好的。
馒头搭糕的日子波澜不惊的过去了好几个月,然而有一天,古太太却神色紧张的把我叫了去。
从前去古太太家都是客厅沙发的待遇,那天,古太太却一直把我让到了她的卧室,坐在卧室的长滕椅上,还没欣赏完古太太卧室的典雅布置,古太太已经从床前小柜子里拿出一合包装异常精美的巧克力塞到我手上。
吃了几块巧克力,又聊了会花园里的家长里短,看着古太太心不在焉的样子,怕她有什么事情要去做,我赶紧把剩下的巧克力吃完,起身准备告辞,古太太却一把拉住我的手,古太太纤长的手指冰凉。
古太太指着卧室里的那个红色的梳妆台,压低了声音问我”这个是你们公司的东西么?”
提起这个梳妆台,我不由的变了脸色。
这个梳妆台,其实根本不是公司当初配置的家具,说起它的根源,不得不追溯一下民工小唐的历史。
小唐是江苏常洲人,当初跟着包工头在花园做装修,等到装修一结束,小唐因为勤恳,又熟悉所有的线路铺设,就被留下来做了维修工,好歹算是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年过30的小唐,因为穷一直没娶上媳妇,身上件破西装,还是当年出来闯荡的时候家里给制的,经常从寒冬腊月一直穿到第二年的春暖花开。
那年小唐的奶奶过世了,小唐回家尽孝,看见奶奶留下的老家具都被叔伯们要扔掉。小唐觉得这个梳妆台虽说不是什么好木头打的,却也雕花刻朵的十分精致,当年奶奶的嫁妆之一,一方面舍不得扔,一方面想找个机会感谢公司留下他,于是一根麻绳一捆,硬是背到了上海。
看在小唐诚心诚意的份上,虽说觉得不吉利,我还是让阿姨们洗擦了一下。恰逢当时荞麦和石油搬了出去,就放进他们的空房间,没过多久古先生伉俪就住了进来。
现在看着古太太神色紧张,我想坏了,难道是阿姨们嫌脏,没打扫彻底?要么就是古太太见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虽然脑子里转过无数的念头,也就电光火石一瞬间,我冷静下来,跟古太太解释说这是我们老板上次去苏州乡下旅游,无意间碰到这么个古董要卖,虽说不是什么好木头,却是民国时期的东西,做的又精致,就买回来配在这里,整个花园就这么一个……
没等我说完,古太太又拉住我的手,急急忙忙打断我:我和古先生都很喜欢也,你帮我们跟公司说说看,卖给我们行吗?
一瞬间,我想,小唐今年可以换件新棉袄了。
古太太咽了一下口水,盯着我说你看,3万块行不行?
一刹那,我决定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我都要先把东西从小唐手里花50块买下来,再3万块卖给古太太。
看我楞在那里没了反应,古太太急了再加点也可以啊!
我咽了一下口水,说容我回去和公司商量一下好么?
古太太把我一直送到门口,殷切的看着我离去。
回到物业,看着小唐破旧的衣衫,我叹了口气,直接把古太太的意思告诉了他。
小唐还没反映过来,老李先过来拍了一下小唐的肩膀发了发了你发了。
阿姨们七嘴八舌的感叹着,小唐已经只会傻笑了。
半个月后,小唐拿到3万块辞了职,回家娶媳妇去了。
古太太接下来在一家古董店又买进了几件”老家具,工人搬进来的时候,我看着其中的一个小时侯写作业常用的那种写字台问价钱,油光满面的老板悄悄说:卖给这个台湾人1万块,你要的话我还有,500块给你弄一个?
终于有一天,惧内的古先生发了火。限制了古太太再买这样的老家具。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古先生,何尝不是眼光锐利,看透世情呢,不过是爱她,疼她,所以怕她,让她罢了。
古太太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和古先生大吵一场,而是呆呆的看先生发完了火,然后静悄悄的去煮了一碗面给古先生。(虽说古太太只会煮一碗这样的面,但古先生却幸福的立刻没了火气)
不敢再买古董的古太太,只好在家里练毛笔字,抄抄女儿经之类的。过了一年,就吵着回法国去,据说是法国的古堡要重新维修了。不看着实在不放心。
古太太搬走后,四号楼的一楼空了很长时间,成了我和老李、阿姨们中午吃饭的天堂。
我们坐在古太太留下的舒适的大沙发里,感慨着古太太这样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小的时候有父母疼爱,去法国留学认识了古先生又成了古先生手心里的宝。虽然没有相貌佼好如同小章,也没有热辣身材如同荞麦,却有着最最幸福平安的一生。
(三)英俊多情的威廉王子
鸦片楼上的房子是个有尖顶的复式,因为租金太高,空了差不多有半年没租出去,直到有一天,中介带了个年轻的法国男人来看房。
看到那个男人的第一眼,我有触电的感觉。
无法形容他的英俊,金色的头发,水汪汪的黑色的眼睛,浓密的长睫毛,尖挺的高傲的鼻子,柔和的下颚,从脸的上半部分来看,很象罗马假日里的派克。他身上带着点贵族的气质,很随意的看着房间内奢华的陈设,听到10000美金的报价眉毛都没抬一下,懒洋洋的,眼睛里闪烁着三分不耐烦。
我很惊讶他为什么有黑色的眼睛,所以我一直怀疑他的血统里有中国的部分,他甚至会上海话。看到房间里的古董佛龛,他说了第一句话:满好看的。
威廉王子在两个星期后搬了进来,和别人都是司机送过来不一样的是,他是由公司人事行政总监亲自陪过来的。
老李的香烟总是在客户入住的时候派发的特别勤,一盒香烟派完后我们基本能得到了租客所有的八卦。然而那天大概是人事总监在场的缘故,老李的投资略显失败,我们只得到一条比较爆炸的信息。威廉王子工作的这家也算赫赫有名的公司是他的家族企业,由于不听老头子的话,今年才被赶到到这家最没有发展前途的上海分公司来。等老头子消了气再回去。
威廉王子入住的当天下午,就有了一位访客。一个非常清秀的上海小姑娘(长的有几分象章子怡)。她的拜访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与威廉一起上班。
没出一个星期,小姑娘的来历老李就摸就清清楚楚了:她是威廉公司的前台,见到威廉的第一天就直接去了威廉住的酒店,然后留了下来,然后就住了进来。
小章子怡确实有几分姿色,最有风情的是她的头发,几乎每天都要换个发型。有一天早上盘了个发笈,让花园里两个民工看走了神。
然而小章每个月总有不在花园的那么几天。而那几天里,威廉一定会有其他年轻貌美的访客。而这样的拜访也一定是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小章子怡请我去了卧室,送了一盒YSL的粉饼作为礼物,寒暄了几句后,小章直接了当的说:能不能请保安先生控制一下威廉的访客?不要让一些无聊的人来骚扰他。如果有这样的访客,你能不能偷偷告诉我一下?
我看着小章年轻美丽的面庞,心底惟有一声叹息。
小章后来越发住的勤了,轻易不肯离开,而她早上的上班时间,也由从前的9点变成了后来的12点甚至2点。吃过阿姨做的午饭后,化完精致的妆容才打个的慢慢赶过去。
威廉的人事总监在容忍了两三个月终于发声音了。具体的内容不得而知(老李的司机朋友也是在公司里道听途说来的)。但是威廉那天是铁青着脸回的花园,小章没有同行。
威廉开始给阿姨指令,不要再帮小章洗衣服或单独做饭了。小章开始看威廉的脸色了,有时候威廉还会要求小章回去住几天,因为他想静一静。(但从访客的情况看,这种安静太过奇怪)
威廉的房子有时候会传出小章哭闹的声音,但是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却是安静的,威廉冷漠的走在前面,眼睛里透露着三分不耐烦,而小章紧紧的跟在后面,化着精致的妆容,对我们露出幸福的微笑,有时候笑的多了,那笑容就僵在嘴唇上。
两个年轻美貌的人,也贪恋着彼此的年轻美貌,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一点的爱或同情。在上海奢华的花园别墅里,挥霍着彼此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