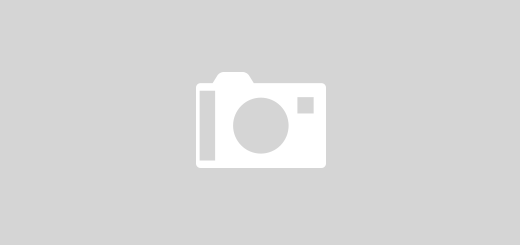保姆是情人雇用秘密侦探(1)
那一刻,她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勉强张开眼睛,看了看护士怀中蜷成一团的小家伙,是儿子,她重重地吐了口气,然后又疲惫地合上眼。她觉得唇边应该有一丝淡淡的微笑,因为一家完全属于她的咖啡店已经在向她招手了,可是她又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微笑的情绪,相反心里沉甸甸地堵得慌。
以上那幕发生在1999年6月17日。
且允许我们隐其姓名,把上文那个刚刚做母亲的女人称为小许。在若干年前,小许及她的“同类”们被我们这个城市用三个字概括着:金丝雀。如今这批“金丝雀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恩宠,被赶出了“金鸟笼”;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小许那样,非但仍然呆在鸟笼中乐此不疲,还为“主人”们生下了孩子。
她们就是我们此刻要描述的特定人群,针对她们如今的状态,我们暂且给她们一个“升级换代”的称谓———金母鸡。
财产比儿子更让人踏实
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记者坐到了小许的咖啡店里,与她进行了一番随意的对话。
如果小许不告诉记者她的真实年龄,记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穿着品牌套装,留着微卷长发,一脸干练的女人才二十六岁。当然,不要误会,小许的皮肤相当光洁,整张脸找不出一道纹或一颗斑,记者之所以会觉得她三十出头,完全是因为她的那种神情。
你很难从这种神情中看出些什么来,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被巧妙地隐藏起来,这样的老道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才二十六的女子。
“你先坐一会儿,等我把今天下午的帐算完。”说这句话的时候,咖啡店外正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大约七八分钟后,小许合上面前的帐本,舒了口气:“终于算完了,每天都要这样忙几次。”
“为什么不找个会计呢?”记者不禁发问。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算心里踏实,再说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会计专业。”小许微微扬起脸,有点自嘲地笑了。
小许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读大学的时候她找了一份在酒店、舞厅做洋酒促销小姐的兼职。在一家现在已经停业,但当时十分出名的“迪吧”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威森的男人。威森是台湾人,三十多岁,在上海做高档礼品生意,有点身价。
“我起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将会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更没有考虑过做所谓的“金丝雀”,当时就是本能地出于对钱的崇拜,很自然地跟了威森。”小许用很淡的口气说着这样的话,手缓缓地用精致的银勺搅拌着面前的咖啡,这时她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小许冲记者笑笑说:“保姆说我儿子午觉醒过来要找我,我叫她把他抱下来。”记者在后面与小许的交谈中才知道,小许与儿子、保姆平时就住在咖啡馆二楼的一套房间里。
小许和威森的同居生活过得很平静,威森时常回台湾,但无论多忙他都不会忘了给小许“生活费”。
“有时是三千,有时是五千,”小许有点感慨地说“对于一个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同时他又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因此我觉得特别满足。”
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小许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正在一家银行实习,对未来的生活正充满了憧憬,所以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打掉这个孩子。
可是威森怎么也不同意,他在台湾虽然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但是他再想要一个儿子,他许诺小许:只要她替他生个儿子,他就帮她开一家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店。
于是,1999年6月17日,一个男孩出世了,小许给他取名叫旭旭。同年年底,小许的咖啡店开张了。
“女人吧,有时也挺奇怪的,旭旭出生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用来交换理想的一样东西,可是看着他渐渐长大,慢慢地学着咿咿呀呀,感情就开始浓厚起来。”小许从保姆手中接过儿子,熟练地抱着他。
“那现在威森还常来上海吗?”记者忍不住问。
“隔月会来一次,时间呆不长,一般一个多星期就要走,他现在这里的生意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多数都交给手下的人去管理。”从小许的脸上,记者看不出她对威森去留问题的意见。“他对旭旭挺好的,每次都不忘记给他买一堆礼物,对旭旭该穿什么尺寸的衣裤记得也特别清楚。今年6月份,旭旭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他还特地为他开了一个生日会,在一部分朋友和亲戚间公开了他和旭旭的关系。”
旭旭是个皮肤白白,脸圆圆的男孩,因为长得像小许,所以很中看,依偎在小许怀中,他骨碌着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这家咖啡店上,因为我知道自己才二十六岁,还是一个要拼搏的年纪,威森帮我开了店以后就不是很定时地给我钱了,所以想要以后长期过富足的生活,我只有依靠这家店了。”小许的脸上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金丝雀”应有的慵懒和茫然,她的脸上全是冷静与精明。
“对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满意吗?”记者本来是想问她以后是否会有结婚的打算,但最终忍了下来。
“还不错吧。目前除了爱情与婚姻,我什么都不缺,我甚至已经有了儿子。”小许的脸上浮起一层难以琢磨的表情。“我相信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不后悔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它们都是经过我理智的思考的产物。”
不知道小许现在所谓的“不后悔”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几十年后,她是否仍然能轻描淡写地称自己可以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有,她的儿子是否对此也会满意。
三个孩子,三个男人
在没有见到林林之前,记者就已经对她的故事十分熟悉了,因为但凡知道她故事的人,都觉得那种经历简直离奇到古怪与可笑。
她在古北新区有一套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房子,她的银行存折上有着七位数的存款,她还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她现在跟着一个男人,他是她所有男人中最穷的一个,是浦东一家高级饭店的总厨,月收入刚过万元。
认识林林是在徐家汇的一家火锅城里,上个月,记者的一个朋友过生日,请了几个人一起吃火锅,请来的人中就有林林。林林长得很娇小,皮肤很白,眼睛很大,衣着很摩登,是那种让人挺喜欢的类型。
林林现在的男人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加上林林又有三个孩子,因此朋友常常嘲弄她家快开托儿所了。每当这时,林林一点也不回避她的过去,也没有半点难堪,相反她总是神情嚣张地与朋友就这个话题大声调笑。她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放得开的女人。
“林林不要太结棍哦,生一个小孩存折上就多一百万。”饭桌上,一个朋友这样取笑林林。
“那侬也去生呀。”林林大笑着回答。
林林搭识她生命中第一个“大户”的时候还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的前台小姐,那是个四川人,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连锁火锅店。林林对那个男人还是动过真情的,她曾经幻想那个男人终有一天会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娶她过门,可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她偷偷怀上他的孩子,试图对他进行要挟时,他也只是冷静地给了林林一百万,以作了断。
那以后林林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孩子可以用来换钱,却不一定能成为要挟男人的武器。于是第二次、第三次,林林一次次成为有钱男人的“金丝雀”,也先后替三个男人生下三个孩子。可悲的是,他们都给了她钱,没有一个人留给她感情和名份。
随着孩子的增多,林林名下的财产也多了起来,别墅、汽车,一样都不缺了,可是她心里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她把孩子都丢给保姆,自己整天上美容院、健身房,或是找些人打麻将。不用工作就能衣食无忧,也许很多人都幻想这样的“好日子”,可是林林却在这种生活中渐渐麻木了一种叫“快乐”的感觉。
在和林林接触的几个小时里,记者明显发现她常常把“阿拉小张”挂在口边。虽然记者的朋友一再告诉记者,林林和小张也只是玩玩的,可是记者分明发现林林对小张还是有极大的依赖性。
“林林到现在对自己小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小学还是搞不清楚。”小张把这事拿出来当笑话告诉饭桌上的人。
“那有什么稀奇,这些孩子已经挺有福气的了,有吃有喝,要什么有什么,还不够啊?”林林一边白小张一眼一边夹了一筷子菜往他碗中放。
“那么多小孩,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啊?”终于有人忍不住问。
“想那么多做什么?”林林不耐地回答:“反正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嘛。”
于是记者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一个保姆的三种身份
向来在我们的印象中,保姆就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带好孩子管好家务。然而在记者近期对一些“金母鸡”的采访中,发现很多“金母鸡”家的保姆却并非这样“简单”,比如小祁家。
生个孩子不是小祁的初衷,坚持要孩子的是她的“供养者”朱先生。
朱先生是香港人,认识小祁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结婚多年,膝下有两个女儿。
朱先生很认真地对小祁说:“只要你给我生出一个儿子来,我不但养你一辈子,而且会尽我所能让你过得好。”
小祁将这句话反复把玩了许久,终于决心为他生个儿子。说来倒也争气,一生便真的生出个儿子来,欢喜得朱先生不知该如何才好。
于是,按照承诺,朱先生替小祁在上海西区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子,同时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
一开始小祁并没有意识到保姆阿媛身上还隐藏着朱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只是隐约觉得自从保姆上门以后,朱先生对自己的行踪开始掌握得越来越清楚。几点去做美容,几点去打牌,家中来了些什么人,甚至接到什么男人的电话……这一切朱先生都会在交谈中隐约表露。
后来,有一件事让小祁渐渐把疑点集中到保姆阿媛身上。
有段日子她的一个男牌友似乎对她表示出一定的兴趣,在她家打牌时,每次牌局结束都不肯和大家一起走,总要留下来陪小祁多聊上几句才肯告别。
不料这样的情况没过多久,朱先生从香港回来后到她那里的当天就找了个机会,有意无意地说:“今天倒没有约人打牌啊,不是有几个很聊得来的牌友吗?”
“后来我终于知道阿媛除了从我那里支取一笔保姆费以外,还从朱先生那里支取一笔侦察费。”说这样的话时,小祁的脸色已经十分平静,但是从她不自觉紧握的双手可以看出,当初发现这一事实的经过一定是曲折而激烈的。
“于是,在他回香港后,我把阿媛叫到面前,单刀直入地说:‘你倒是很听朱先生的话啊,他到底给你多少钱了,你把我每天的行踪都向他汇报?’起初,阿媛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口气也吞吞吐吐起来,可是她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拿过朱先生的侦察费。”小祁缓缓吐出一口气。
记者采访小祁的那天,阿媛也在,她似乎忙里忙外地操持着家务,看管着孩子,一刻也没有得闲的样子。不知道小祁的这番话她是否听到。
“直到我答应给她双倍的钱,让她以后不再泄漏我的真实行踪,每次向他汇报的内容都由我来定以后,她才慢慢承认自己的确担负着向朱先生汇报我行踪的任务。”小祁显然对为了自己的“自由”支出一笔“反侦察费”这一举动感到挺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