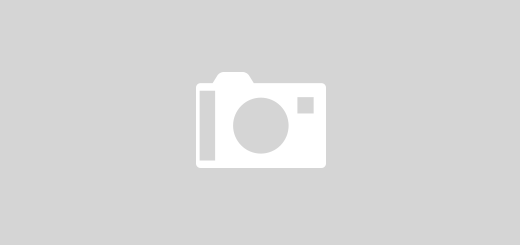一夜能有多少情?(1)
所有那些大张旗鼓地泛滥淹没我们眼球的所谓 一夜情,其实都是美其名曰,充其量都是一夜性罢了。那样目的明确,索取昭然,当人与人之间剩下如此苍白的关系,撇去真情,只留取舍,抹掉爱恨,只取快乐。如此关系,像华贵鱼翅之于寻常人,对不起,你很好,但我总归只能吃米饭一辈子。
记得《东京爱情故事》里永尾完治说过一句话:莉香,让我来背负你的未来,太沉重了。莉香一个巴掌过去,伤心致极。这个巴掌是应该的,当感情没有背负,便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何意义,谈什么真情,不过是轻飘飘的过眼云烟。
所以你看,在2003年底掀起一场网络风云的木子美《遗情书》事件,终致博客红透半边天,注册用户直升十万。
木子美,曾任广州某杂志社的性专栏作家,21岁时怀孕,被男人抛弃,之后经历不同男人,以每周换一、两个的频率历经四年。25岁的这一年,在个人博客上点名道姓地写出与中国某一摇滚歌手的一夜情,其后被大肆转贴而名声大作。
她用她的身体和文字揭示了这样的一种颓丧的生活状态。然而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生活的女人不计其数,只不过是她写出来而她们选择秘而不宣。
且不论此事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单单就此事掀起的风浪,便足以窥见一斑,一夜情这样的事件在人心的灰暗处像一只蠢动的乌鸦,聒躁一时却遮遮掩掩。
一夜情,想来,应该还是有情的成份在里面。这个单词很悲伤,很激情很凄凉也很美。像情人这两个字,它原来是美好而激越的,到如今,更多的却成了二奶的代名词。
一夜情这样的一个词,本应是值得欣赏的,可遇不可求的。它应该是徐志摩的《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汇时,交互的光亮。应该是电影《廊桥遗梦》里,罗伯特金凯与弗朗西斯卡的相拥共舞,致死以完美的姿态保守着年轻时那一夜的两情相悦。应该是电影《情人》里的中国男人与他十六岁的法国情人之间的缠绵,那么温柔,那么呵护,是在越南河岸的车上,他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去握那法国少女的手,那么矜持,那么小心,是在多少年后,他依然想她,记住她的微笑,记住她的气息,告诉她,他爱她,一直,始终,永远。
是的,它真的不应该这样放纵的,形而下的,如此麻木的身体接触。这样的接触,充其量只能叫一夜性,何情之有。
而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事实,木子美的存在只是少数,毕竟生活更多的是需要阳光而不是黑暗,人心更多的是向往真情而不是纵情。相信执子之手,相信情有独钟,相信温暖的可能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慰藉。
这样的一夜情就像烟花,一样的短暂,一样的不会谢,但会散。烟花美丽,却有谁知其夜空背后的黑暗与丑陋,在短暂的激情与长久的厮守之间,总是有取舍的。关键在于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如若任黑暗裹去明亮,任放纵代替承诺,如若我们不再谨守任何的规则,无须坚持,无须践诺,一切有如麦当劳里的快餐速食,纯粹只为果腹。那便再也不用提爱情两字,任心一寸一寸灰去,连微光都熄灭,日复一复,再也不谈你心换我心,再也不谈永远有多远。
这样的关系,多荒凉,便有多心灰,当世界只剩下取舍,只剩下躯体。
都市的森林,人都脆弱敏感,海派的文化,真情在坚强的伪装之下。
人到底是害怕寂寞的,由此而引发出诸多的欲望。只是孤独寂寞都不是借口,红尘滚滚,谁不须把持悲欢?
我想念一个时代,白衣似雪,笑容纯粹。那时花开,你说执子之手,不离不弃,你说亲爱的亲爱,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