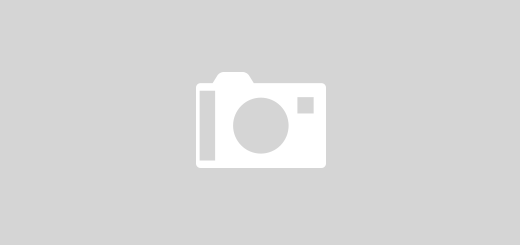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爱上小我十岁的女下属 我真想鼓起勇气向她告白……
几天后我又和同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我没有给她打过一次电活,却在无数个夜里长时间盯着那个终身不忘的号码。我知道我在吞噬无奈,同时也在扼杀一个少女的无限情思。
年轻女孩,坐在我对面
1999年,我离家到深圳闯世界。在一外资企业苦熬半年,才进入中层管理,做人事主管。深圳这个火热的南方城市,充斥太多昙花一现的,我时刻告诫自己努力工作就行,不要陷入什么漩涡。
随着公司效益剧增,我的事务越来越多,迫切需要一名助手。我委托办公室代招一名助手,要求中文专业,男女不限,但一定要懂粤语。
一个星期后,我出差回来,一位女孩坐在我办公室的副台上。白皙的皮肤,略带几分土气的衣着,束在脑后的马尾,一看就是刚出道的大学生。从她的举止谈吐看,有可能还来自贫困山区。
我信手拿起桌上的工牌,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可是,英文名却是“麦当娜”。我又好笑又好气,问是谁给起的这个愚蠢洋文名字。她一脸无奈而又怯生生地说,是办公室主任写的。我无奈地摇摇头,那是总经理的亲戚,没办法,那就算了吧。
刚开始,她也确实让我头痛。因为她那带有浓重广西腔的粤语,让我这个本来就对粤语头痛的人更头痛。有时急了她就一个劲地“嗨呀(是的)嗨呀”,“我几(我知道)我几”的,气得我两眼冒金星。但当我看到她满脸涨红地咬着嘴唇,我的余怒就消失了,渐渐滋生出一份怜惜之情。
慢慢接纳,却小心翼翼
巨大的工作量像石头一样压在我身上,令人身心疲惫。我的女助手却像一株春天的箭兰,生机勃勃,每天都热切地期待着下一个任务。
有时,我们加班加到晚上十点多钟,我就带她去楼下茶艺厅消夜。也不知从何时起,我竟然喜欢看她吃饭的样子。她那不施脂粉的脸红扑扑,眼睛清澈明亮,时而眨巴几下,然后又安详地望着碗里剩下的食物。那清纯的眼睛,让人不由想起山涧小溪。慢慢地,我心里接纳这个女助手。我不再那么抱怨加班,她也因为和我的配合越来越默契,而变得开朗起来。
一次,我的胃又痛起来,只得用手抵着胃按压。她走了过来,变戏法似地从抽屉里拿出一瓶胃药,冲上一杯广西特产罗汉果茶,幽默中又附和几分腼腆对我说:“头,仁慈的上帝已把药丸放到你的抽屉,你吃了一定会疼痛消除。”望着这个还有几分天真的女孩子,我平生第一次服用了胃药。不知是药物作用还是精神作用,胃疼真消失了。“谢谢!”我很感激地对她说,她却装模作样比划着让我感谢上帝。
从那以后,我们空闲也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她是广西人,生长在一个离越南不远的贫困山区,姐妹有三个,她是老大,是父母用一万余元借贷培养出他们祖祖辈辈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她必须要挣钱,为妹妹交学费和还借债。
多想靠近,却只能远离
我越来越喜欢她身上的聪明和质朴。我想帮助她,照顾她,但我又不得不疏远她。
第二年,因为成绩突出,我被调至另一部门。离开那张熟悉的办公桌,我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一个月后她也被调来了,仍然坐在对面我办公桌的对面。一切还是那样的默契。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签错了一张出货单,如不及时处理,会让公司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心急如焚赶到机场找到客户。当处理好一切回到办公室后,精疲力尽的我一阵难受,竟然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几天后我又和同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我没有给她打过一次电活,却在无数个夜里长时间盯着那个终身不忘的号码。我知道我在吞噬无奈,同时也在扼杀一个少女的无限情思。
我醒来已躺在医院。“你怎能这样玩命呢?”她搓着双手站在病床前说,显得局促不安。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眼里充满爱怜与担忧。她又端来煲好的莲子银耳汤递给我,一种熟悉而又久违的感觉流遍了我的周身。
担心影响工作,第二天中午我便找到医生要求出院,却得知她预付了全部费用。我说能不能退费出院,医生说:“你的身体还很虚弱,再说也得用完已开出的药后才能出院。”这时,一位护士在一旁逗趣地说:“你看你,都把你女友急哭了,费用都交了,你嗦啥呀。”我愣住了,张开嘴巴想解释,终究什么也没说。
面对女孩的痴情,想到家中的妻儿,我不由得痛苦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周后我出院。第二天就去银行取了3千元钱交给她,然后向老板递交了调离申请。一个月后,老板让我去沈阳搞市场调研。
临行前晚,我把她约到一家海鲜大排档,告诉她明天我要去北方。她静静地看了我很久,才说:“你是因为我而走吗?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爱你,同时你也失去了被我爱的资格。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喜欢你……”大排档有些吵,我却听得一清二楚。她说得很吃力,也很平静,一行清泪从她美丽的眼角溢出,跌碎在她那白底碎花的连衣裙带上。
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我没有能力给予她未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怎么能忍心让一个小我十来岁、无辜善良的姑娘,去和我一起承担呢?
永不再见,却永远怀念
在北方,我夜以继日忙碌,没有给她打电话。一个多月后,我带着一份可行性报告悄悄回到南方。
在办公楼的出口处,我看到了清瘦得有点苍白的她。我们对视了十几秒,我清楚地看到她面颊抽动了一下。然后,她很艰难地向我挤出一个微笑,再毅然转身,快步消失在出口处……那一夜我在厂区的草坪上徘徊到深夜。
几天后我又和同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我没有给她打过一次电活,却在无数个夜里长时间盯着那个终身不忘的号码。我知道我在吞噬无奈,同时也在扼杀一个少女的无限情思。
半年后,我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但我的胃病已经不再是几颗药丸抑制得了的。那年初冬,我告假回乡。
住院期间我向电话问候我的同事问起她,同事叹了一口气,说她半年前就辞职了,据说已回南宁了。同事还告诉我,她把我留在南方的东西都收藏在一个箱子里,寄存在同事那里,半个月前还来过电话,问我回来没有。
我拼命拨打她的电话,可是已经停机。后来,我也往她家乡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
我和她的故事,埋藏在我心里已经多年。我时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太残酷了呢,无论是对她还是对自己?直到现在,我偶尔会望着天边,默默地呼唤:“对不起,你现在好吗?”
来源:女娲之爱 love.ngnvip.com 口述实录 love.ngnvip.com/category/koushush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