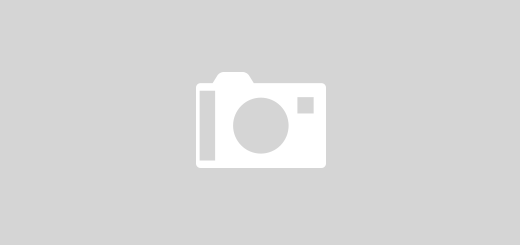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爱情小文章:好紧好爽再浪一点—太满了 h……
※
搬入新宅的第一日不是个晴朗的天气。
翕忽的空气窜流得过□□疾了,仿佛塘中休憩的鱼虾倏然感知到被破坏了的磁场,急着寻一个出口却仍只得被困囿,方向感在一片昏茫中全失,灰原哀在这个诡秘的夜晚失眠。
她迫使自己合上眼睛,却无法自制地想起些因太过久远而几欲忘却的前事。
潮湿空气氤氲的屋子弥漫的气息分明与从前的那个不同,可她偏偏想了起来当年那个屋子里的气味——多的是令人作呕的酸腐腥味,还有粗粝的铁索缠绕在腕上,洁白纤细的手腕平白多出了乌青色的划痕,仿佛一道道薄纱似的腕带。
她想要有一个镜子。这么想着便失声笑了起来,Gin抬头深望她一眼,Vodka警觉地直起身子。她想,这么紧张做什么,我只是想要一个镜子。
这样就可以看看孱弱地将近失却全部气息的自己的模样是不是很美。
Gin走近她,长而冰凉的手指抚上她的面颊,指尖顺着下颌的轮廓划过去,她莫名觉得那酸腐的气味更加浓重了,窜入她的鼻腔里面,麻木许久的嗅觉竟有了复苏的迹象。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添了份恶心,告诉她死可没有那么容易,请想想你是落入了谁的手中。
她冲着Gin挑衅地笑,银发男人的狠戾容色蕴藏在唇角勾起的笑里,逗留在她下颌的手指蜿蜒下滑至脖颈处,猛地收紧了虎口。
突如其来的窒息感让她的感官再度失敏,她拼了命地大口呼气,而脖颈上的大手却越收越紧,直至她连反抗的气力都无。末了那人说:“Sherry,你是个聪明人。可偏是聪明人往往活不太久,因为聪明人总是太信自己,而不信命。”
然后那只手抽离,Gin向Vodka看了一眼,听话的跟班便随在身后走出门去。她张大了嘴巴呼气,大肆起伏的胸口像得了呼吸道疾病一般疼痛,犹自借着最后一口气息对着男人挺拔的脊背说:“我却是太信命,不信的是你。”接着便一阵猛咳,背向他的男人顿住脚步,回头望她。
她讥诮的笑意从未如此阴森可怖,面上的血渍散发出八寒地狱的孤清,Gin站在那里,终是什么话都没有说。不知是为那句太过冷漠又太过通透的话,还是为那淤泥之中挣动而生的红莲一般过分妖冶的美丽。
后来有一天,她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缩小了的身子不复往昔凹凸有致的窈窕,只是一副初中女学生的模样,毛利兰往身上套着制服站在她身后,对着镜子摆正头上的警帽,又匆匆离去,开门欲走前突然回过身,对已成为灰原哀的她说:“很美。”
然而那始终不是一份舒适的美。常会有褒奖却难以得到发自真心的喜爱,因为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说——That’s too much.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笑出一副单纯亲善的模样,她的美丽里带着刳骨剔肉一般残酷的血色,就像一朵艳烈的红莲,笑出的泪水如同甜蜜的□□,远观即可,走近了是要付命的。
她给自己筑起一道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把所有尝试进入的人都堵在外面。她用尽办法告诉自己,不是害怕被别人伤害,而是太怕伤害了别人。一切都太好了,神明不该对她如此宽容。这不是她相信的命运。
她的胸口生出了已淡忘许久的熟悉的挫痛,一阵汹涌的风又把她席卷入更遥远的过去里,宫野明美的面孔出现在她眼前,她的耳际只能听到呼呼作响的风声,便拼命注视眼前那个她最爱的人的的脸孔与口型,宫野明美在说,志保,我爱你。
至此她终于呜咽着哭了起来,泪痕沾在面上清晰的触感仿佛□□室里流淌的新鲜血液,令人作呕的腥腐气味清晰可闻,可身至其间的时候她只是淡漠地想,看看,这都是你们没有见过的人间。她想要捉住宫野明美的手可那人却越来越遥远,她哭着叫她的名字,在身后跑却怎么也追不上。她停下来的时候宫野明美也停下来,还是那样悲伤的神情,无声地说着,志保,我爱你。
后来宫野明美的面孔也消失了,交互重叠的是毛利兰与工藤新一的脸,熟悉的笑容里竟然也掺入了不可名状的悲怆。他们长得何其相似,他们原本可以很好。刹那之间她感到一阵眩晕感袭来,势不可挡地,仿佛偏头痛再度发作,却直接跳过了漫长的前奏,直接跨入了涛浪一般湍急的疼痛的中心。她想起了毛利兰的手指柔软的触感,与Gin冰凉的指尖划过下颌的触感是两个背向的极端。那双手覆上她的太阳穴,不轻不重地按压,不停不休地过去数个小时,一旦停下她的眉头便皱起来,于是那人没办法一样地叹息,又再度继续。她用心体会着疼痛随着那人揉动的节奏逐渐远去,可并不肯说“停下吧”。她只是迷恋那人指腹的温暖。
醒过来时头痛得过分,像亲历了一场真实的病症,偏过头看见津田莎朗正坐在她床边的高凳上一脸担忧地望着她,这才想起,方才过去的是迁来新居的第一个夜晚。
“你哭了。”津田莎朗说。灰原哀想,真是个单刀直入的开场白。
“只是做了噩梦。”灰原哀说。停顿一下又补充道,“非常可怕的梦哦。”
含着笑意的神情却做出一副受惊的模样,灰原哀对这样的伪装驾轻就熟,她以为就要看到津田莎朗松口气的样子了,却不料她的新室友只是定定地望着她,神色未见轻松,过会儿拿起床头装了热牛奶的茶杯地给她,温声道:“喝吧。”
灰原哀接过杯子津田莎朗便站了起来,走出门后又折了回来,几步走回床边,双臂撑在灰原哀床榻的边沿,盯紧了她的眼睛。灰原哀方要向后仰时她倏然笑起来,直立起身子,对显然万分疑惑的人说:“没关系,我会等你亲口告诉我。”
灰原哀心头一紧,似未全然反应,讷讷问:“什么?”
津田莎朗又恢复了以往嬉笑的神情,是轻快的语调,回答道:“你的故事。”
※
此后毛利兰又忙得不顾朝夕了好一阵子,服部和叶见毛利兰多日未与她联系,便选了一个周末的晚上登门造访,铃响了五六声后门开了,毛利兰的面容满是惫色,服部和叶把双手拎着的袋子送至她目前,笑说:“什锦煎饼和手握寿司。”毛利兰略显苍白的脸才染上了些微红的光彩。
“怎么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的确是睡了一整天,如果不是你按门铃,恐怕现在还醒不来。”
服部和叶满目担忧:“又连续几天没睡吗?你大病初愈,这样拼命不行啊。”
毛利兰笑了:“什么大病。”
服部和叶这才想到,比起枪弹在她身上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迹,区区一场切除术又算得上什么伤。
毛利兰到厨房去,从橱柜里拿出两罐速食汤来,朝服部和叶扬手示意——“要吗?”
服部和叶的眉头揪起来,朝她摇头道:“不要。”又道,“想起我过去每次到东京去,都不愿在外面吃饭,那些都不如你亲手做的好。”
暗黄灯光下毛利兰的脸沉静而温和,嗓音依旧轻柔,仿佛说着一件旁人的闲事:“可我们都知道,‘当年’的意思是已经过去了。”
服部和叶唇角勉强牵起的笑有些苦涩,她呆望着厨房内毛利兰的背影讲不出话来,那个人专注地往汤杯里冲水,袅袅升起的白色雾气将简装修的屋子冷硬的线条变得多有些柔和,那是人间烟火的味道,一种令她无法不强迫症一般一遍一遍回想过去的味道。这样分明而决绝地昭彰着此前重重譬如昨日死,而她想看到的却是“今日生”。
“你不该离开那个小孩的。”服部和叶说。
“她不是小孩。”
服部和叶笑:“习惯了,就总是忘。”
从灰原哀搬去与津田莎朗同住后,毛利兰与她的联系比之从前渐少了,一是此次追的案子案情实在重大,连睡觉的时间都无,更无暇顾及其他。二是,在这段时间里,灰原哀也未有一次主动联系毛利兰。只是她精神紧张地忙了太久,竟对此浑然未觉。
此时被服部和叶提起,毛利兰才惊觉已许久未得灰原哀的消息,困倦的脑袋顿时清明不少,当下拿起手机拨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没料到听筒内传来几声“嘟——”后,电话竟断了。
毛利兰微蹙眉头,心下想着会否这时灰原哀有什么急事,接听电话多有不便,约莫过了五分钟又重播过去,却还如头次,只是这次断得更快了些,只听得一声响便再无声息。毛利兰这才感到有些怪异。
毛利兰拨通吉田步美的电话,得知吉田步美正与小岛元太和圆谷光彦三人一起在阿笠博士家陪他聊天,光彦此时正与他下国际象棋,为的是转移博士的注意力以避免被他无聊透顶的冷谜语纠缠。灰原哀并未与他们在一处。
吉田步美将津田莎朗的号码传讯给毛利兰,毛利兰便即刻拨了过去,电话很快通了,津田莎朗的声音听来气息有些不稳:“兰姐……我们正在路上,灰原她喝醉了……我在扶着她拦的士。”
风的呼啸声令听筒里的话不那么清晰,毛利兰只捕捉到了“喝醉”两字怒气便起来:“她喝酒了?!你知不知道她的身体……”
话未说完听到了灰原哀隐约的声音,毛利兰将音量调至最大,听见她问津田莎朗:“是谁?”飘忽的声调里有浓重的醉意,“是不是……小兰姐姐。”
毛利兰正鼎盛的怒气突然之间泄了大半,她有些想笑,灰原哀在神识不清的时候,叫她小兰姐姐。
像是进了什么密闭的空间,电话里的声音一下清朗起来,津田莎朗又接起电话,说:“抱歉,我们刚坐进的士。”
“不要紧。小哀呢?”
“她沾上座椅就睡着了。现在不省人事。”
毛利兰深吸一口气尽量不让自己发怒,向津田莎朗道:“回去后给她冲一杯蜂蜜水,强制她喝下去。她太容易偏头痛,如果还是发作了,她的药一般放在大衣的内袋里,给她吃一粒就可以。替她把窗帘拉紧实……如果必要,用大拇指深按她的太阳穴,用些力气。”
津田莎朗静静听着。
“……拜托了。”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毛利兰迟疑地问:“在听吗?Sharon?”
许久,津田莎朗道:“你不需要拜托我。灰原对我而言是非常亲近的人,就如同她与你一样。”
毛利兰没有说话。
“再者,我想兰姐你现在一定在生气,气我为什么带她去喝酒,可我要向你辩白一下,因为我并没有带她去喝酒,只是把她带回来。”
毛利兰面容泛出微微的红色,才说出两字“抱歉……”就被津田莎朗打断,她接着说:“而灰原孤身一人去喝酒,你猜是为了什么?”
像一场簌簌的白雪落入了心里,盖住苍原上最后一丝苟延残喘的生气。
像一双怪兽的利爪扼住了咽喉,拼命想要出声却吞吐不得,最后恍然发觉那桎梏来自自己。
津田莎朗说:“你能回答我吗?你知道答案吗?”
毛利兰听得见那似是冷静的语气下近乎压迫的诘问:不能。还是不敢。
她的沉默令瞧着她的服部和叶也觉察出异样,向她投来询问的目光,她不知该怎样作答,不论是向服部和叶还是向津田莎朗。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被人当庭对质一般问出了这个问题,这个她在心中问了自己无数次,又回答了自己无数次,却终究不得宣之于口的问题。
“你爱她吗?”
毛利兰的瞳孔倏然放大。
服部和叶走时什么也没有说。
毛利兰自然未告知她电话内容,她也没有追问,只是离开时回头深望了毛利兰一眼,用一个近乎叹息的眼光。毛利兰感激地朝她笑笑,与她说再见。
阖上眼时天地落幕,可那冷漠的声音在她耳畔不住洄游打转,一开始是津田莎朗的,后来是灰原哀的。
迷蒙的混沌间灰原哀的声音清晰得有些过分,像是她真的就俯身附在毛利兰耳端,带有热气的呼吸喷在她脸上令她感到不适又舒适的痒,那样迷惘地问她:“你爱我吗?”
“我爱……你呀。”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men.ngnvip.com
文章来源:女娲之汉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