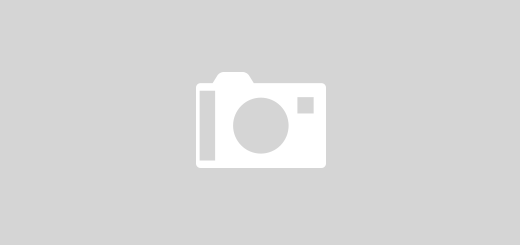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情感故事:荡翁乱妇小说—霸道总裁肉宠文高质量……
卢珍打小就被娘亲教育:做人不能太失败。太失败了就像你爹爹——没那么大的锅还愣配那么大的盖。为了侠义,用自己的儿子,就是你这小兔崽子,来顶替来历不明的孩子去送死。要不是你展叔叔赶来得及时,看你爹他后半辈子有没有儿子给他养老送终!
他娘数落起他爹来,总是絮絮叨叨,一词不变。而他爹总是陪着笑脸听着,边捋他灰花的颚下三缕,边诺诺地念着“娘子说得对,娘子说得既是。”
卢珍有五个叔叔。其中四个是江湖上声名赫赫的五鼠中的另外四个。第五个则是当今皇上钦封的『御猫』——展昭。
老鼠和猫,猫和老鼠,本应该是势不两立的对头,可卢珍打小就见到据说是最大的猫跟他们家一窝耗子厮混一块,弄得他很长时间都有其实自然界的猫和老鼠是很友好互助的一对动物的错误认识。
卢珍的爹爹和四个叔叔既然被并称为五鼠,那江湖上的称呼就自然都带有『鼠』字。像他爹爹就叫『钻天鼠』,
据说,是因为爹爹没多大本事却很爱充大头菜,遇到什么认为不平之事都要去管一管;见到陌生路人有困难委屈都要去帮一帮;若是给他飞天彻地的本事,怕他是天庭都要窜一窜去给救母的沉香搭把手。
据说,某人三番四次替他没有多大本事偏好管闲事的爹爹救场之后,忍无可忍地跳脚道:“你TMD的是一只钻天老鼠就别充什么豹子头!”
于是他爹爹『豹子头』的名号还没来得及在江湖上打响,就被某人擅自替换成了『钻天鼠』。
后来,人人都知道了五鼠中的『钻天鼠』是卢珍他爹爹卢方,卢方是『钻天鼠』,反倒没人记得卢方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威风无比的江湖称号——『豹子头』。
后来的后来,那个总是帮卢方救场的某人英年早逝,没有办法再及时出现替他善后。那个某人为卢方救了一生的场,英年早逝得忐忑不安,不安他这么一走,卢方接着就被他的事妈性子害得跟下地府。于是他硬是在弥留前给他讨了个媳妇,找了四个兄弟,并称五鼠。
不过后来的后来的后来,『豹子头』这个名号也响彻江湖,不过那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是被另一个跟本系列全然无关的人夺了去,便不在此累言。
卢珍的二叔是『彻地鼠』,三叔是,三叔是……
——娘,三叔是什么鼠来着了?
——他还能是什么鼠?撞山头撞傻了的呆老鼠呗~
——哦,谢谢三叔母告知小侄,不过……三叔母……您走路乍没个声呢?
——霍霍霍~~~大侄子,不懂了吧?叔母这是身轻如燕纤巧弄尘凌波微步(下略N字)……
——……(==)
再说,卢珍的二叔是『彻地鼠』韩彰,三叔是『穿山鼠』徐庆。
据说他们在跟卢珍的展叔叔称兄道弟前,是很不待见他的,认为他弃了江湖投了官门,做官家的鹰犬丢江湖的脸。所以他们在跟卢珍的展叔叔称兄道弟之前,对他乐此不彼地行落井下石之举。
据说,卢珍是生在他爹娘回陷空岛的路上的。他爹娘带着刚出生的他回陷空岛的第二天,陷空岛就遭遇了兵船压境。
据说当时芦花江上的兵船连成黑压压的一片,弓箭手一人射一只火箭就能把陷空岛烧了,穿铠甲的一人踩一脚就能把陷空岛踏沉水里。
卢珍曾偷偷地领两个弟弟做过试验,他们一人一箭只烧掉了五叔的竹林内的一颗紫纹翠玉竹;一人一脚,只踏断了展叔叔供养在荷花池边一尺高神坛内的神像中的小黑狗。能把陷空岛烧了沉了,乖乖,那得多少人啊?没等卢珍惊叹出个所以然,三个小鬼就被他们的爹娘紧急送往茉花村的丁家避难半年。
据说那天领头的是一个大官,很威风,好像是朝廷的一品大将军什么的,生前还是上过战场杀过外敌战功赫赫的。
卢珍的娘亲和叔母们每每说到这个据说,都表情不一,可继续往后说的时候,都统一成了一副神往赞叹。
据说,领头的大将军涂善带兵压境陷空岛,为的是一个比卢珍大些的婴孩,摆的是“不给就围剿”的威风。撇开涂善好声好气说明缘由或许卢珍的爹爹和二三四叔就背着他五叔偷偷把孩子给他带回去交皇命的可能性,基于卢珍爹爹和四位叔叔乃是侠义至上的真男人大丈夫,断断不会做出将一无辜的孩子送到屠刀下的恶心事。
据说那天陷空岛的渡口是横尸遍野,流出的血把芦花江都染成了红色。
卢珍只见过朝日夕阳把芦花江染红的样子。他总是想像着那天爹爹和四位叔叔抵抗大将军的威武英姿,一边送上他崇拜的神情扩大他二三四叔的扬扬得意,一边奇怪为何他爹爹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
据说,那天他爹爹和四位叔叔终寡不敌众,一番恶战后就不得不再次面临是把孩子交出去还是被人灭了岛再搜出孩子的艰难选择。
一边是侠义,一边是亲情。
卢珍的爹爹卢方善于牺牲自我的豪情无限澎湃起来,他毅然用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刚出生没几天刚回到陷空岛第二天的卢珍顶替了那个被涂善索要的婴孩,也就是卢方被卢珍的娘亲含泪叨骂了一辈子“哪有人这样当爹的”的失败。
卢方了解卢珍他娘的委屈和害怕,他自个当时要把顶替的小卢珍交到涂善的屠刀下时,也心如刀割,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吞。
据说,当时小卢珍离涂善的屠刀就差了一寸;据说,当时涂善面露狰狞的佞笑;据说,当时他爹爹卢方和二三四叔都痛苦不已,一个痛苦自己的儿子,三个痛苦无能为力维持的侠义;据说,当时卢珍他五叔漂亮的眉头拧成了麻花,画影锵地先卢珍一步跟涂善的屠刀进行了亲密接触。
——白玉堂,你们五鼠莫不是想反悔——?
——少把你白爷爷做的事摊到别人头上!涂大将军要孩子可以!断了白爷爷的剑再说——!
据说,当时卢珍他五叔跟涂善是打得天地无光昏天暗地地动山摇。
——得,爷爷成孙猴子了。
——哪里,玉堂只是成精的老鼠,比大圣还差着点火候。
据说从来都是不被外物干扰地说啊说。
据说,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劲风破开纠缠相拼的刀与剑,定睛一看,竟是一杆舟船的帆杆,斜插入石,露出的部分剧烈抖动紧张的空气。
据说,一道朱影自江面踏帆疾来,犹如一道疾风吹散了陷空岛上紧绷沉重的气压。高挑的身量往卢珍他五叔和涂善跟前一站,朱红官服被江风拉扯显出精瘦,面不带笑更显一双黑瞳清亮澄明。
来的不是他人,正是皇上的『御猫』——展昭。
据说,卢珍他展叔叔稳稳地往卢珍他五叔和涂善跟前那么一站,左手拿剑侧放身旁,右手平举持一明黄绢轴,口中喝道:“侍卫亲军殿前司骠骑一品大将军涂善接旨——”。好轻易好随意好威风好气势地退了围剿陷空岛的水兵,救了卢珍他的小命一条。
据说又据说,卢珍打小听着娘亲和叔母们的据说长大。每次据说到最后,总会被他娘亲或叔母们教育:做人啊,不能太失败。但做人啊,也不能太成功。太成功了就像你展叔叔,老是被奇奇怪怪的人缠上,连个媳妇都娶不到,这辈子算是完了。
五个叔叔里面卢珍玩得最来的是他五叔,五叔的脑袋里似乎有用不玩的点子,跟他五叔在一块永远没有无聊的空当。但卢珍最喜欢的却是他展叔叔,跟他五叔相比,他展叔叔有时候会安静得乏味。可只要在他身边就会有很舒服很安心的感觉,就是乏味的安静也能听到细小的虫鸣,沙沙的风歌,陶陶然,醺醺然。
某一天,卢珍在书上读到“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当以身相许”一句后,福至心灵,兴冲冲地寻到他展叔叔,扑过去,搂住接住他的展叔叔的颈项,豪气干云道:“展叔叔娶不到媳妇也不用怕这辈子完了。等珍儿长大了,珍儿嫁给你!”
平地惊起千层浪——
——五弟不要啊!
——五弟放下剑!放下剑!
——五弟!那是珍儿啊!是珍儿!
——五弟!小孩子家不懂事乱说话,别激动别激动!!
卢珍没有听见四周乍起的混乱,他只看见他展叔叔温和的轻浅微笑,他只听见他展叔叔清和好听的声音对他说:“好啊,等珍儿长大了展叔叔还没取到媳妇的话,就娶珍儿当媳妇。”
卢珍顿时又醺醺然陶陶然,凑上在他展叔叔的脸颊上吧唧了一下。
——展小猫不带你这么不厚道的!!!!!
——冷静!五弟冷静!!!
——珍儿快跑!展昭快带珍儿跑!
——五弟有话好好说!放下剑!先放下剑啊!
于是陷空岛比卢珍更幼的那几个小鬼听到的据说又多了一个。
据说,某一天的夜晚,卢珍被他爹娘慌不择师地送到了茉花村的丁家拜师学艺。
据说,一直巴望着卢珍长大习得他一手金环大刀的卢方每次收到卢珍的家书都老泪垂垂,喃喃叨道:“儿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战场是很危险的,快回家吧。”
×××××××
小一辈听的据说再多,也比不得老一辈亲身经历来得实在。
那日在陷空岛的渡头,卢方的喉咙就这么被纠着天庭地狱兜了一圈。他很感谢展昭的来到,保了他的儿子一命。圣旨什么的,放一放再说,卢方抱起襁褓中的婴孩,轻轻蹭了蹭他娇嫩的小脸蛋。
展昭左手拿剑侧放身旁,右手平举持一明黄绢轴,眉头稍蹙,口中再喝:“圣旨到!侍卫亲军殿前司骠骑一品大将军涂善接旨——”
涂善若有所思地瞥了大呼气的卢方一眼,黑绒披风一震,单膝跪下。
在场众人,无一不跪,白玉堂狠狠剐了展昭一眼,收剑矮身,雪衫擦尘却膝不触地。
展昭展开手中绢轴,清声念道:“门下:着侍卫亲军殿前司骠骑一品大将军涂善,功绩卓着,堪称良才。然朕早误信谗言,致使东宫太子流亡民间。故命御前带刀行走四品护卫展昭寻回太子,接迎回宫。旧旨既废,望归。宜令准此。”阔袖翻飞,隐隐可见他的小臂白布紧缠,潮红浸散,掩去宁愿是风吹惹起的微颤。
“臣涂善领旨谢恩。”涂善不甘愿地起身从展昭手中接圣旨。
白玉堂先一步拿了圣旨丢给涂善,一把抓住展昭右手碗朝胸前一带,灼烧他掌心的热度更是让他狠狠瞪着展昭道:“你手上这伤是哪来的——?”
展昭眸中一颤,想抽回手臂,奈何白玉堂握地紧,稍一使力更是牵扯到筋骨撕裂剧痛。他佯装平静,疏淡道:“多谢白兄关心,可展某还有公务要办。”
“呵,也是。”涂善慢条斯理地卷起圣旨,眼扫展昭和白玉堂,嘴角上扯,意味深长道:“太子在我手上还是在展昭你的手上,都是一样的……”
“展某不明……”
展昭一凛,话未说完就被白玉堂抢过话头冲涂善不耐吼道:“这没你涂大将军什么事了,领了圣旨爱上哪上哪待去!”
“白玉堂……”涂善咬牙切齿地挤出白玉堂的名字,厚重的黑绒披风扯风一震,头也不回地鸣金收兵。“展昭…这事没完!你好自为之!”
“展某自知,涂将军一路回京先行走好。”展昭右手不便,只好左手持剑做了个请。待到涂善远走,方松了神。但觉眼前一阵彩光大作,竟乎得站不稳。要不是握着他右手手腕的白玉堂及时揽住他的腰身,怕他就要直愣愣地摔倒在渡口坚硬的大石上。展昭按了按额头,冷硬的巨阙贴着皮肤没能让他感到一丝冰凉,“太子……”他困难地往怀抱婴孩的卢方那边探道。
卢方听言,一愣,道:“啊?这不是太子。”
展昭余毒未清,被柳霁月的刺铃穿透的手臂缠紧了绷带才勉强能活动,一路行来都高烧未退,昏昏沉沉地睡在马车内。适才赶到芦花江边时,惊知涂善带兵围岛,他等不及舟船慢行,待离外围兵船十丈开,便生提了真气,射出船家的舵桨,空中两度借力,硬撑着内力深厚踏帆急奔往渡头,在目睹涂善跟白玉堂短兵相接时,更是折了一杆船杆注入十成内力破开两人。柳霁月的毒中后,不能动武更不能动气。忌惮毒而动弹不得的男子被抓得容易,奋力抵抗的也迟早因为毒攻脑髓如坠炼狱,终失了神智。这原本就是她神女教炼制傀儡鬼人时用来捕获优良种子的毒方。阴辣狡猾得紧的毒,却有个极易好解的法子,中毒者只需接连浸泡在寒水中三个日夜便可。展昭浸了一夜寒风暴雨,虽染了风寒,引起高烧,可毒素总算是去了大半。剩下几日不说他尚需赶路,就是无事依他的身子状态也吃不消再在寒水中浸泡两个日夜。此刻他是头脑刺痛昏涨,周身骨头宛如被人碾碎再起来一样。废了气力赶来,乍然听到卢方回了一句不明不白好似玩笑的回答,口气不由不善:“展某不懂,还请卢岛主留下太子!”
“唉~?我大哥说不是太子就不是太子。展小猫别以为你救了我们兄弟就可以横了!是不是你引来的官兵还不好说!”
“哼!早就听说你不知好歹做了官家的鹰犬,现在就来会会你这丢了江湖脸的败类!”
韩彰和徐庆摆出看家武器张牙舞爪地叫嚷起来。
白玉堂一直银牙紧咬,不出声,任着展昭行他所谓的公务。若不是展昭只小小尝试了一次便不做挣扎地将身子交给白玉堂撑着,涂善没走白玉堂就要劫了他离开。
反正他白五爷不是第一次做劫人虏拐的行当。
展昭气血翻涌,眼前一黑,便虚软了身子。
画影撩开韩彰的铁抓、徐庆的大锤,白玉堂接住展昭人事不知的身子揽入怀中,骂道:“吵什么!没看他受了重伤吗?”
徐庆、韩彰听了,面露窘迫,展昭救了陷空岛是事实,被他们气得昏了过去也是事实,虽然他们只是小小地轻轻地说了两句微不足道的话。可见到白玉堂维护展昭,还显然对那被他虏劫回来给陷空岛惹来祸端的婴孩身世一副知之甚晓的模样,两人心下就不是滋味,嘴硬驳道:“他是猫,我们是鼠,他受伤关我们陷空岛什么事?”
卢方心里也是酸溜溜的,看展昭欣赏不变,但却不怎么顺眼起来。直觉韩彰和徐庆说得有些过了,但也不开口阻拦。加上瞥见一向足智多谋的老四『翻江鼠』蒋平也只是摇着鹅毛扇,不言不语,更做了沉默。
“不关陷空岛的,但关我白玉堂的事!”白玉堂恼火地夹抱起展昭,轻功尽施,往岛中庄园方向疾奔。
“哎——?老五,这又关你什么事——?”徐庆不明,连忙冲着白玉堂的背影大吼问道。
远远传来白玉堂越来越小的声音回道:“这猫还欠我一条件没说!欠我一比试没完!欠我一约定爽了约!他欠我的东西多着,怎么不关我的事——?!”
白玉堂这一走,留渡口静了一片。
蒋平摇晃鹅毛扇,敲敲发愣的韩彰和徐庆的脑袋,问道:“老五这说的是啥,两位哥哥听明白了吗?”
两人困惑地摇摇头。卢方宝贝地抱着他儿子,也不解地凑上问:“老四啊,你说老五说的这都是啥?展昭欠他东西了?我记得盗了开封府三宝还有抢了太子回来的可都是我们家老五吧?”
蒋平慢慢捻了捻他两撇光滑的小胡子,做高深莫测状道:“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佛曰不可说啊不可说。”说罢,摇晃泛黄的鹅毛扇往岛中走,唤道:“三位哥哥,走了,回家啦。大哥你把小侄子抱出来,再不回去大嫂该急坏了吧?”
“啊——!”卢方一声惨叫,他刚才竟然把家中因为他把儿子抢出来送死而哭闹着要上吊的媳妇给忘记了。他抱着卢珍,往家中狂奔,边奔边叫:“秀秀——!不要想不开啊——!”
“大哥——等等我们——”
渡口一众龙套到路人的伤残的可怜的悲哀的被遗忘到九天十地之外的陷空岛的仆役家丁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互掬把辛酸泪,相互搀扶把家回。
如果给他们一句台词的机会,他们会说:“别把龙套不当人!”
如果在这之前加一个期限的话,他们会希望是 —— 从开头到结尾。
×××××
白玉堂不讨厌展昭。
展昭不是一个能令人讨厌得起来的男人。识得他越深,越讨厌他不起来。就像没有人会讨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泡一池暖暖的热水澡;没有人会讨厌在困倦的时候有张舒适的床让自己安心躺下好好睡一觉。展昭就是那种会令人有喧嚣尘世里找到避风港的感觉的人。他明明年纪不大,但个性却沉稳温润;他的身量明明并不粗壮,但却能撑起一方天地;在他身边不会有压迫的感觉,似乎就这样就好,不用担忧,不用烦恼,静一静也好,闹一闹也好,展昭这个人都会温和地笑笑,然后包容你所有的任性,给你所有想要的沁静平和。在他身边可以做你自己,不用顾及,因为他不会惊讶你的本性,也不会指责你不应该这般。
白玉堂也不喜欢展昭。
展昭的温和是源于淡漠和疏离。他就跟猫一样狡猾,有着极为柔顺的外表,巧妙地保持着让人亲近的距离。似乎你可以摸着他的皮毛抱着他感受到令人流泪的温暖;却永远触摸不到他心脏真实的跳动。
展昭的包容则是因为他的冷情。他并不将你放在心上,所以你如何表现他都会温和地笑着,看着,当作那就是真实的你,认为你本该就是如此。他对你不报期待,自然就不会失望。你在他身边不会有负担,因为他对你并无所求;而你对他的索求,他能给的,决不吝啬,反之不漏分毫。
白玉堂不讨厌展昭,白玉堂也不喜欢展昭,白玉堂只是不爽展昭,不爽不爽很不爽。不爽他透过自己看向另一个人;不爽他老是迟了他们的约会;不爽受伤的是他,难受的却是自己;不爽舒服躺床上的是他,傻呵呵守在旁边的是自己。
“爷爷是哪根经不对了,自讨苦吃地来伺候你这只臭猫!”白玉堂骂咧咧地给展昭换了身干爽的里衣,笨拙地给他颈窝处夹好棉被,一双老鼠爪子忍不住捏住展昭的双颊狠狠地往外拉,弄得爪下之人发出痛苦的唔唔才啪地松开。
“死猫臭猫,让你占了爷爷的紫檀木床还让爷爷伺候你!”白玉堂恶狠狠地摔下话,大张大阔地挑开堆漆杞梓木挨桌坐下。全然忘记早些时候看见曾抱着太子逃出宫的阿敏和对岸茉花村的丁家三妹月华一起出现时的惊讶;和把她们推出去时自己理直气壮地说:“展昭现在躺的是白五爷的床,爷爷担了就是。而且,他这伤病要时常换衣擦身什么的,你们两姑娘家总不能看了他的身子,污了自个的闺名吧?”
以白玉堂的性子会主动提出照顾一个人,还是月前气得他白五爷跳脚的御猫,实属诡异。可白玉堂渡口上的神情举动,一二三四鼠也是看在眼里,叹了句“不打不相识”也就由着白玉堂去了。陷空岛上下宠白玉堂是宠惯了的,别说他五爷主动提出照顾的是一个大男人,就是一黄花闺女他们也会同意,然后一边盘算媒婆聘礼去。
阿敏是早羞红了脸,告了退。
月华和白玉堂打小认识,也算青梅竹马。
有些人见一眼,就倾了心,托了情;有些人相处一辈子,也起不了波澜。
丁家月华贤淑美好,白家玉堂少年英雄,两家也是世交,两人却从来没那个心思。
对白玉堂而言,丁月华很好,却是太好了,跟她在一起很累,总怕糟蹋了她,委屈了她。
对丁月华而言,白玉堂很好,却不是她想要的那个人,他太耀眼,无法让她安心,见到他,她看不到两个人会在一起生活的样子。
可展昭不一样。初见时的温文尔雅,再见时的英姿飒爽;他体贴地只挑了她的耳饰让她服了输;他细心地一直站着,为坐在烈日下陪两位哥哥垂钓的她遮起一方阴凉。
与展昭相见不多,却让丁月华失了一颗女儿心。
母亲做主,给她和展昭定了婚约。她记得他微微一愣,然后一礼,温和淡笑道:“这是展某的福气,随太君做主。”
那时展昭才初出江湖吧?她和他都稚嫩得似乎能掐出水来。
丁月华掏出一绢方帕,轻轻地为展昭抹了脸上的薄汗。江湖风雨,这人的面庞还是这般俊秀好看,却硬了几许棱线。
或是白玉堂盯着她的眼神太凛厉,丁月华收了方帕,轻道:“五哥言得极是。”未出阁的女儿家,饶是未来的夫君也是不能失了礼数。她向白玉堂福了礼,又轻道:“昭哥就麻烦五哥代为照顾了。”
白玉堂给自己倒了杯茶,怎么喝味道都不对,似乎茶水里都溶了空气中轻轻的女儿香。他含了几口,咽不下,又吐了出去,烦躁地置下茶杯,跳到窗槛前,推开窗扉,让扑面的凉风吹散莫名的烦躁。
吹了好一会,白玉堂自认恢复了平素的自在,心神一回,转头瞥见展昭整个人裹着被子缩成一团,面泛潮红,双唇艳红干裂,低低好像在呢喃什么。白玉堂凑近一听,断断续续的似乎磨的是“冷”字。
白五爷终究是欠了照顾人的经验,他猛然想起大嫂给展昭看病后叮嘱过,展昭是内寒外热,千万不能再着凉了。白玉堂连忙手忙脚乱地翻出自己的裘皮披风,给展昭盖上,又拍头想起他应该先把窗户关山,省得灌风。折腾一通,白玉堂都起了一层薄汗,身上压了厚厚一层衣物的展昭唇瓣间还是断断续续地磨着“冷”字。
白玉堂累了,半身赌气地爬在展昭身上。
你不是冷么?
爷爷大好男儿给你当被盖了还冷不冷?
或许是白玉堂的体温高,或许真是就差那么一层保暖,白玉堂压在展昭上头后,展昭的冷颤渐渐停了,难受拧起的眉头也渐渐舒展。
前夜梨花树上候了展昭一夜。今日又对上涂善围岛。更别说伺候了展昭一通更衣净身。
白玉堂累了,他压在展昭上头,眼见展昭渐渐舒开眉头,露出平和安静的睡颜,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两个哈欠,三个哈欠……不安份地挪啊挪,不知不觉就挪到床里头;不知不觉就挪到了层层衣物和棉被里头;不知不觉就抱着展昭,给他自己的体温取暖,索取他的温暖,渐渐入了酣睡。
白玉堂这觉睡得深沉,一宿无梦,到天泛亮,白子进来换茶水了他才朦胧醒来。
“五爷早安。”白子换好桌面的茶水套杯,又重灌了壶暖水在脸盆边暖着,目不斜视恭敬给白玉堂请安。
“唔……”白玉堂揉揉眼,眨巴两下还有有些迷糊,鼻音夹带睡意地哝道:“唔……你下去吧……没叫你就不用进来伺候了。”
“是,五爷。”
白玉堂坐在床上发了好会呆。他坐着把棉被扯开道缝隙,凉风顺溜地往内灌,展昭昏沉中觉到失了温暖,又受了凉意,身子不由一缩,自然而然地往热源靠去。展昭转了个身,不想正压倒了右手的伤口,浑浑噩噩中叫了声吃痛,才把白玉堂从惊醒。白玉堂帮展昭放平了身,跨过他下了床。
白玉堂原没打算跟展昭一块睡,便没换身歇息的里衣,直接裹了外衣睡了一宿。再好的料子睡了一宿也皱了,白玉堂想都没想,换了身整洁,便懒懒趴在心爱的金丝楠木雕花桌二号上,啜了杯茶,彻底清醒他漂亮可错了根经去照顾猫的脑袋。
卢方哄他媳妇哄了一夜,终把她哄乐了,原谅他为人父却失败的举动。
放松了心,也就想到了他的结义五弟白玉堂,和也算救了他儿子卢珍小命一条的展昭如何了。
卢方八方螃蟹步稳稳一迈,迈到了白玉堂的泽琰居。到了门前,他举手欲敲,便听房内低低传来展昭喘不上气的嗓音:“白玉堂——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一直相伴的还有布料磨挲的声音。
接着亮起的是他五弟白玉堂像压着什么,或贴着什么,使得听上去如同隔了一层般痞赖的话音:“欺负你又怎么样啊?你现在啊~反正是只病猫~我喜欢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你~!”
展昭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卢方僵硬地举着手,敲也不是,不敲内力又恰好足够他听清内里的声音。
一会,房内传出新的声音。布料磨挲的声音,间或夹杂蹦蹦两声较重的撞击声,还有白玉堂扬扬得意又暗夹嘶哑地嗓音:“你看你,现在躺在床上,跟一堆烂泥一样…不仅是一只病猫…也是一只臭猫…还是一只任人摆弄的笨猫 ……~”
展昭呼吸更重,两息才长长地重喘一下。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小猫儿还想反攻爷爷…~?来,爷爷让你左手~这边…攻我这里……~”
“唔……嗯……”展昭重重哼了两声,却听一阵肢体摩擦布料引起的挣扎声,接着是重物落到棉被上的闷实的声。
一会,就没了声音。
再一会,“……猫儿?展小猫?展昭?展护卫?展大侠?”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哎!你别这么没用啊!展昭——!”
房内一阵混乱,急促响起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愣是在卢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砰地跟开门冲出来的白玉堂撞了个对。
“大哥?!你站这挡道干嘛?!”
“五弟……我……”
“没空说这个!大嫂呢?!”
“在药房……”
不等卢方说完,“……煎药呢。”白玉堂已经掠了身去。
展昭第二次醒来的时候,白玉堂的房内少了白玉堂,多了丁月华,鹅黄罗衣,似暖烟般美好。
“昭哥,你终于醒了……”她缓缓依床坐下,掏了绢帕轻轻为他擦拭额上的虚汗。“渴么?可想喝杯茶水?”
展昭微微点点头,就着她的手,喝了半杯温茶,润了喉咙。少许茶水透过嘴角,还没流过下颚,便被绢帕轻轻拭去。
展昭左手拈袖,别扭但自然地轻轻拭去滚过丁月华面颊的眼泪。
展昭的动作很慢,眼泪落得太快。
终有漏过的,落入了棉被,渐渐浸染开一片湿意。
丁月华隔着绢帕覆握住展昭为她拭泪的手背,细细压抑的哽咽到底控制不住地放了出来。
有人用了一辈子去明白展昭,有人却只用了一个月。
于是用了一辈去明白展昭的人,爱了一辈子,痴了一辈子,得到了他的半辈子的人。
却也仅仅是人。
于是用了一个月便明白的人,却因为太过明白而热了情,冷了心。从而赖了他一生,毁了他半生,苦了彼此千年万世,又哄得他重头追他而来。
据说,卢珍记得最熟的词是韦庄的《思帝乡》。在茉花村丁家的时候,他时常能听到丁家三姨在一个人轻轻哼唱。
春日游,
杏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年少?
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
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
不能羞。
纵被无情弃,
不能羞……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men.ngnvip.com
文章来源:女娲之汉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