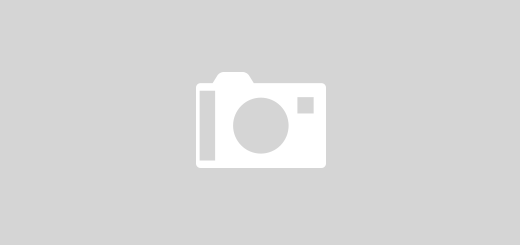一个48岁男人的忏悔(1)
朱子墨是我的真名。
只所以我敢将我的名字这样毫无顾忌地张扬,那都是因为今天,我已真正放下了所有所谓的“忌讳”,要向一个女孩用我痛彻心肺的忏悔,对她说一声“原谅我,小令!”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两年前的今天,小令那双哀怨地眼睛,当她将冰冷的手从我的掌心抽出转身而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一走,她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了。我想喊她,可终究还是没有,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是无奈,还是生命中太多无法承载的爱?
我的手在空气中无力地垂下,那一刻所有曾经与小令一起走过的日子都化为记忆的碎片变成泪水从我的眼里迸出。
(一)相识
2000年的时候,我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老总。
那一年我44岁。
那年初春,出版社新招了几名编辑,25岁的小令也在其中。小令是那种很能让男人心动的女孩,清纯可爱,无论见着谁都展着一张十分甜美的笑脸。小令的出现,好像唤醒了我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时候爱上小令的,我已记不清楚,只知道,忽然有一天开始,她便满满地占据了我的心。
整整一个春天,我几乎夜夜失眠。那些辗转反侧的黑夜中,在我的脑海里、眼睛里跳动的,都是小令的身影。
小令她现在在干嘛呢?
小令她可睡了?
小令是在灯下编稿子吗?
那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每天近在咫尺,却让我的思念如草般疯长。我好像自己回到了十几岁的青涩年纪,在暗恋的饥渴下日日被兴奋、惆怅以及各种各样难以名状的心情一天天吞噬。
小令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的隔壁,过去,我几乎从不走进去。可是自从心中有了小令,时不时我就进去“视察”一下,或是发份传真或是拿本资料。编辑部的李大姐每次见了都巴结不已:“哎哟,啥事体要朱总侬亲自来忙哦,这种事体阿拉来帮侬好了!”
我的心思无人知道。
就像李大姐说的那样,我现在越来越顾着单位的事儿了,从前一天都是难得见着我人影的。
小令有感觉吗?每次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不是专注地敲击电脑就是在批阅文章。好像有那么一两次,她转过头朝我微微一笑。每当这时,我总会开心不已,哪怕就这么远远地看着她也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对,那段日子即是煎熬也是快乐。
很久以后,当我有一天和小令说起这些时,她把脸埋在我的颈中,温润的唇瓣滑过我的皮肤。“我有感觉,子墨。我知道你喜欢我,就像我一直偷偷喜欢着你一样。”
(二)相爱
在这个开放的年代,到了这个成熟的年纪,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是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可我却一直没有,好像一直在坚持,直到遇上小令。
可是我不能放开身心去爱她。因为我是个有家室的男人。
我的妻子阿芬,就像很多出生于50年代末,在上海亭子间长大的女人一样,贤惠而温婉。
结婚十五年,她一直任劳任怨细致入微地照料着我和儿子的生活,孝敬公婆和睦家人。应该说,我的 婚姻是平和而美满的,至少和阿芬那么多年走来,我们都从未红过一次脸。可我,或许就与天下很多男人一样,不甘于平静的日子,总想能从波澜不惊里活出点精彩来。很多时候我也在想,对于阿芬,整整十五年要说没有爱那不可能,可我很爱她吗?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对阿芬,从来都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一切好像都是水到渠成,到了适婚的年龄,取妻、生子,走着凡人必走之路。
五个月后,从黄埔江吹来的风已有一丝凉意了。翻开从前的记事本,我找到了载有那一天的记录:“今天是2000年8月11日,我约小令去了茂名南路的安尼斯茶馆,第一次,我吻了她……”
似乎这么多年来的坚持就是为了这一天的来临。从那天起,我和小令迅即相爱了,只是我们谁也不曾料到,彼此会爱得那么深切与真切。也是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开始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就像个初尝爱果的小男生,眼里心里除了小令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小令也一样,她说,很多时候她真的忘记了地球还在转动。
整一年多,除了双休日,我们每天早上在某个车站相约一同上班、下班,一起共进晚餐。那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人到中年,终于尝到了 爱情的滋味。我是真的忘了我的年龄与身份,有好几次在傍晚的外滩上,我和小令开心地追逐着,对着隔岸灯火辉煌的浦东高喊。
我们就这样咨意地呵护着宠爱着对方,病了痛了乐了愁了都会牵扯彼此的心肺。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城皇庙烧香,有个算命的朝我们走来,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令,然后扔下一句话:前世姻缘今生定。“我们是前世的爱人,今生再来续缘。”小令对算命先生所说的话高兴了好一阵子。
我和小令从不相信宿命,但缘份确实是个美妙而奇怪的东西,是自然的奥秘还是神奇的黑洞?我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走到了一起,可是却错过了婚姻的时辰,但我们却有着惊人相似的手纹和惊人默契的心灵。
那时我和小令都不知我们的未来会怎样,也从不去想。小令说过,她无意要抢占阿芬的位置,只想今生能和我有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至于我,我是从不敢多想,生怕一想多了,所有的美好都会灰飞烟灭。因为我的身上有太多无法轻易甩开的责任,于阿芬于小令都是。
有一次激情过后,我拥着小令光洁如玉的身子,心中突然有种莫名的酸楚。
“小令,我比你大那么多,你到底爱我什么呢?”
“子墨,我爱你的才华你的帅气你的温情,还有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从你进出版社的那一天起,我就爱上了你,可先前却一直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经配不上你。”
“子墨,我知道你喜欢我,就像我曾经一直偷偷喜欢着你一样。爱情对谁来说都是公平的,从没有谁配得上谁这种说法”。
那一刻我感动无比,紧紧拥着小令,就愿从此凝固成爱的化石。
2000年底,小令辞职去了电视台做编导。
“子墨,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在一起,同一个单位实在有太多不便。”
“你那么单纯的一个女孩我怕你照顾不了自已。”
“有你的爱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小令就这样去了那家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担忧,我担忧美丽的小令会招来一大批追求者,因为我已经44岁,有妻有子,怎么能再敌那些青春的、与小令年龄相当的优秀男人呢?如果失去小令我想那一定会是我今生锥心的疼痛。“子墨,今生除了你,我不会再爱上别人!”小令用她的拥抱来安慰我。
(三)失爱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矛盾,蹉跎了小令的韶华,不能给小令一个美好结果,对她是不是太不公平?因为我是那样深爱着她。可我实在无法放弃。
无法放弃她也无法放弃家庭。
“子墨,你不要离开我,如果你离开我,我会活不下去”。小令伤心的时候总是这样对我说。
小令把和我在北京蒲洼狩猎场游玩时拍的照片剪成一小块放在了随身所带的皮夹里:“子墨你看,我们像不像一对恩爱夫妻?”小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喜欢把我和她所有的合影都摊在床上,一张张地百看不厌。
“小令你这样天天看能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谁叫你每天晚上都不能陪我呢,我只有多看看你的照片啦,我怕一不留神就把你给丢了。”
小令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脸的孩子气,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无奈与渴望,每到这时,惟有把她拥紧来表达我的爱。
与小令相爱的一年多里,无可避免,在面对阿芬时我的罪恶感与愧疚感会如虫啮般不时地刺痛我的神经。可是在炽热的爱情面前我无法让自已考虑更多更成熟,我甚至会侥幸地想,就这样过一天是一天吧。
过一天是一天,可生活哪能让我如此如愿。阿芬还是知道了我们的事情。这种事迟早是要暴光的,看得够多也听得够了,可我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得那么令我措手不及。
那夜,一向好脾气的阿芬如火山般爆发。
“一年了,你居然隐瞒了我一年。你不是说你很忙天天有应酬吗?!”
“她是谁,你们有没有上床过?!”
“下馆子看 电影手拉手逛马路,你心里还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
“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叫我面子往哪搁?!”
我无语,把身子深陷在沙发里。是啊,我还有什么可为自已辩解的呢?一切的辩解都是苍白贫瘠。
第二天还是激烈的争吵。
第三天也是。
面对悲伤到极点的阿芬我除了无言还是无言。
阿芬没错,理亏是我。
我在单位请了五天假,手机也关了五天。我需要冷静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这五天小令找不到我几乎要发疯。
第六天当我把一切告诉小令后,她哭倒在我怀里。“子墨,不管怎样你都不能抛下我啊,你说过的,我是你的至爱你的惟一。”
我抱着小令深深地吻着她,却心乱如麻心如刀割。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懦弱的、自私的男人,当到最后关头当要面临选择的时候,我背叛了我的心。
我不想为我的行为作任何的开脱,阿芬在这场感情的角逐中是无辜的受害者。正如她所说“朱子墨,十五年来我尽心尽意地服侍着你,请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良知与十五年的夫妻情分让我反思,我对不起阿芬。可是我能离开阿芬吗?一个43岁的下岗女人,生命中从来都是以丈夫为天儿子为地,离开我,她怎么生活?
“子墨,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求你,离开那女孩好吗?”几天后,情绪已不再那么激烈的阿芬有一天从半夜醒来,哽咽着紧紧抱住我的手臂。
我终于体会到,选择原来是那么矛盾而揪心的痛。我侧过身,在黑暗中摸到了她全是泪水的脸庞,轻轻抚触着。有多久没有这样温柔地对待阿芬了?心中的歉意无从说起。“早点睡吧,给我时间。”
我始终没有向阿芬承认我与小令有上过床的事实,也始终没有承认我深爱小令的现实。我知道,如果我说了,善良的阿芬会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阿芬最终给了我“自新”的机会,在她看来,这是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她在竭力修复着我们十五年夫妻生活中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裂痕。关键时刻,她以一个上海女人的精明忍耐与宽容,度过了她婚姻里的危机。或许她也明白,这只是一段插曲,只是她婚姻中必需渡过的一条河而已。
此后她一如既往的待我——-每天早上为我准备好早点,当我夜归的时候桌上总有我爱吃的消夜。
面对这样的妻子,我还能说些什么!
一个月后,还是在茂名南路的安尼斯茶馆。
“子墨,告诉我,你们到底解决的怎样了?”
“小令,我真的很无奈!”
“你的无奈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给你很好的未来。”
“我说过我不在乎,我可以一直做你背后的女人!”
小令的伤心令我彻底心碎。我不知我这样一个45岁的男人是否还能经得起婚外恋的折腾。虽然我心里依旧那么深爱着小令!
又过两天,小令从电视台加班出来已是深夜11点。我骑着自行车把她带到外滩。一路上,小令都把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她是那么依恋着我。
我们重复着在安尼斯茶馆说过的那些话,小令哭着,我狠下心不去看她。
“子墨,不要离开我,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子墨你为什么转变的那么快呢,难道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一年多的爱都终结了吗?”
“不是的!”我转过身抓住小令的手,“小令你听我说,你终究是要嫁人的,我不能耽误你啊。让我当你的哥哥吧,我会永远关心你呵护你的!”
“我已经有一个哥哥了,还要你这样的哥哥做什么!”
“再问你一句,要不要我?”
“小令,我真的很无奈。”
小令就这样不可信也万分痛苦的盯着我,眼泪从她的脸上不断滑下。而我的心同样也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
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小令将她的手从我的掌心抽出转身而去。我想喊她,可终究还是没有,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是无奈,还是生命中太多无法承载的爱?
我的手在空气中无力地垂下,那一刻所有曾经与小令一起走过的日子都化为记忆的碎片变成泪水从我的眼里迸出。
(四)寻爱
小令走后的当夜我就被送进医院,医生在我的病历上写着:急性心肌炎。
住院的一个多星期里我天天给小令打电话,可她从来不接,短信也不回。我不知她怎么了,也不知她上哪去了。我原以为我的想法很真诚,即使做不成 情人与爱人,至少当成最好的朋友我还是可以将心中对她的爱化为一辈子的关心来呵护她。
但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令的手机从此再没打通过。
我去她租住的卢湾区大同花园找过她,但房东告诉我她已搬走。
我开始满世界的寻找小令,甚至想,只要能找到她,就与她结婚。因为我终于发现自已是多么深刻地爱着她,如果失去她对我来说,将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创痛。
小令的家人都在海南,于是我托海南的朋友帮忙找,可始终无法找到。
那天在肇嘉浜,我意外碰到了小令的同事陈美。
“你和小令的事我到上个月才听说。小令已经离开上海了,至于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她走前对我说过,你伤透了她的心,这一辈子她都不想再见你。朱子墨,我很同情你,可是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既然给不起她未来,为什么当初还要招惹她?”
陈美对我撂下这几句话后就迅速上了一辆的士走了。我知道,在陈美或者很多人的眼里,我都是个不屑一顾的人,自作受。
一年过去了。
我彻底失去了小令,连同所有有过欢笑与泪水的过去。
生活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机械地重复着每一道程序。我每天朝九晚五地过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日子,激情这个词早就不在大脑存留,而性事,更不知从哪一天起也真正成了例行公事。
一切平淡如白水。阿芬依旧知冷知热的待我,从前的伤害虽经弥补,但还是有它曾经破碎的痕迹,只是谁也不会再提起。夜晚坐在阳台上,我常常看着遥远的天际想着小令,不知她现在生活得好不好。
有句俗语:人世间,有时候你只需要花一分钟便可认识一个人,再花一小时可变成朋友,一天后能成为爱人。可一旦真心爱上,你却可能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将他遗忘,直至喝下那碗孟婆汤。
我朱子墨或许就是这样一个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忘爱的人。我原以为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可是我错了,我一直无法忘记小令。她的一笑一颦都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苦涩回忆。
客厅里有 音乐响起,是上高一的儿子与他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扯开喉咙不知是在念歌还是在唱歌,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快乐的。我听见他们在唱:
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
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
融化在宇宙里
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著你
这样的甜蜜
让我开始相信命运
感谢地心引力
让我碰到你
是什么潮湿了我的眼睛?一个走过了大半辈子的男人,还有什么能让你如此触景伤情的呢?可是,孩子们,你们懂得什么是爱吗?你们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吗?
又是一年。
我远在加拿大的老母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催促着我们尽快去加国。离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这一去,今生还能再见着小令吗。
两年过去了,我对小令的爱还是无法释怀。多少次还在梦中见到那双哀怨的眼睛!
我突然感到自已真的老了,变得那么容易怀旧,容易伤感。
缘起缘灭,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48岁已快知天命的年龄,我还敢再去言爱么?
2004年4月20日将是我举家移民加拿大的日子。今天我又来到了两年前与小令分手的外滩,黄浦江徐徐吹来的风夹杂着微弱的浪涛呼啸,原来我的快乐早已随着江风远逝。
我在心里对着隔岸灯火辉煌的浦东高喊——
原谅我,小令!
原谅我,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