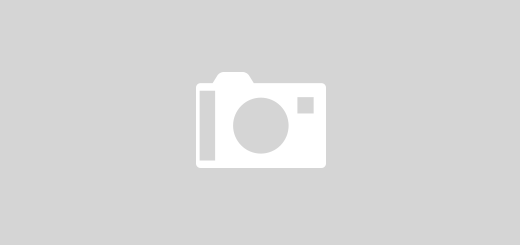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没老婆可养,我想把钱捐给国家_情感文章……
引导语: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在路上。有好几次,雨大路滑,我滑倒到水沟里,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但是不敢停下来。 停下来哪有钱养老婆?
编者按:
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谁的身上。
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人:樊振平
男 ,947年生
湖北省建始县茅田乡兰鸿槽村人
当了三十多年乡村货郎
我当乡村货郎,为了挣钱养老婆
我叫樊振平。这个名字,三十几年前,在茅田一带,十里八乡没几个人不晓得。铃铛叮叮一响,都知道我樊振平来了。
我年轻时候是一个乡村货郎。这职业现在没有了,如今到处是商店,赶个集也方便,年轻人还会在电脑上买东西,用不着货郎了。
山里的乡村货郎和平原地区的不一样,我们交通不便,多半要走山路,不能推车骑车,只能挑个担子走乡串户。我的担子里好东西多,火头针线、锅碗瓢盆、胭脂肥皂、鞋帽布头、包子馒头……只要是村户人家要用的东西,我都卖。
我挑担子,走的地方多。每次出门,一圈走下来,怎么也得两三个月。
那时候走乡串户的货郎不少,我的生意总是不错。因为我讲信用。只要有赚头,绝不喊高价。农民买东西,一分钱都计较,那时候鸡蛋才几分钱一个。我不骗他们,价钱合适,多进几次货,多跑几趟腿,多的都赚到了。有时候人家要买的东西,我担子里没有,就拿笔记下来,下次一定给他们带来。他们信得过我,进货的钱不够了,他们愿意先把钱垫出来。买过我东西的人,没有说我这个人不行的。
别的货郎生意没我好,他们欺负农民老实,卖残次品,卖高价钱。东西价高却不经用,别人试过一次就不会再买,等多久都要等到我去。别的货郎不服气,说我这个人有财运,我说不是,是我不贪心。
● ● ●
年轻时的我,长得周正,个子不算高大,但一副斯文相,见谁都一脸笑。乡里乡亲都说,若不是挑一副担子,肯定都以为我是个区里的干部。虽然我是一个赶脚的,但穿得也干净体面。一九七几年,乡下人大多穿草鞋或自家做的布鞋,一身补丁的对襟衫子,我就穿上了解放鞋、中山装。在那个年代,可是了不得的。到了八几年,我穿得更洋式了,皮鞋配西服,完全是城里人的装扮。
我老婆说我穿什么都好看,是个衣架子,要我穿好点,这样她在人前才有面子。她自己也爱打扮,爱穿新潮的衣服,红红绿绿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眼得很。我也很得意她穿好看,出门看见好看的衣服都给她买回来。
我老婆是龙坪乡申酉坪的人,叫贺月华,小我四岁。结婚前,我父亲专门找算命先生算过,说我们八字不合。我妈死得早,所以父亲很谨慎,反对我们的婚事。是我一再坚持,非她不娶。我是真的喜欢她,她长得好看,又斯文又秀气,是个有教养的女人,读过初小,识字比我还多,她爹当年还是龙坪企管站的站长。
1974年阴历的5月份,我在龙坪的楂树坪挑担子,晚上在老乡老杨家借宿。那天他跟我说,我看你这个人精明能干,为人又不坏,我给你说个亲事要得不?我想都没想就说,要得要得。我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的,没想到第二天他还真的带我出了门,去了申酉坪,他的一个亲戚家。
女方详细打听了我家里的情况,主要是成分问题,还有家庭负担问题。没费什么周折,女方就同意了。老杨给我说的女人,就是后来我的老婆贺月华。当年腊月我们就结了婚。婚后我才断断续续地知道,贺月华在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约,对方是申酉坪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后来人家转正了,去了龙坪小学教书,就毁了婚约。为这个事情,贺月华差点自杀,她父亲在龙坪街上也好久抬不起头来。我这才明白,她条件那么好,为什么愿意嫁给我一个货郎。
结婚后我更加努力做生意,就是想赚钱,养老婆。我不让贺月华下地出工,不让她挣那几个工分,舍不得让她辛苦。就让她在家养着,做点轻省的家务事,主要任务是给我生个娃儿。她自己也愿意这样,很是乐意过这样自在逍遥的日子。可几年过去了,肚子没一点点动静。
挑担子当货郎其实是很苦的。平日穿得体面,不上坡不下地,其实苦得很。起码得有个好脚力,一天就在不停地走,为了那几个钱,再难走的路都要走。而且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东西越是好卖。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在路上。有好几次,雨大路滑,我滑倒到水沟里,东西撒得到处都是,但是不敢停下来。
停下来哪有钱养老婆?
挣着钱了,老婆却跟别的货郎跑了
我不仅当货郎挑担子,还会一点手艺,我会理发,还会泥瓦工。货郎担子里随时带着理发工具,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老乡需要,我就给他们理发,无论老少,统一收五毛钱。有时候也不收钱,能混一顿饭也可以。
最开始挑担子,回家出门都要偷偷摸摸的,不敢声张,夜里要很晚才回去,白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怕被队里拦着不许出去,还要被批斗。后来政策好了,可以大大方方当货郎,没人管。
1983年茅田撤销人民公社,成立茅田区,分田到户。家家户户的日子好多了,至少粮食这一项是不缺了。我还是做我的货郎,很多人羡慕我是个殷实大户,就也学我,搞个担子,走乡串户卖东西,可生意总是不如我。十里八乡都只认我这个货郎,别人卖东西摇拨浪鼓,边摇边喊。我不一样,拿个旧自行车上取下来的铃铛,铃铛叮叮一响,大家就知道我樊振平来了,什么也不用喊,大家都围上来。
生意好,挣钱也快。1986年,我买了一辆嘉陵125的摩托车,花了八九千块钱。别说在乡里,就是在城里也是个稀奇东西。那时候好多地方都修了公路,可以骑车去。好多人都说我骑摩托车当货郎,那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他们不知道,因为跑得快,我赚的钱更多了。那个时候卖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小东西不卖了,主要卖衣服鞋帽。
到1989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万多块钱的存款。我跟贺月华说,我挣钱就是为养你的,存着没什么用,我们修个新房子,让你住好点。贺月华同意,我们就把原来的瓦房木房子推倒了,在原地基上新修了三间平房。那时候全村的房子都是瓦房,就我家的房子是砖混平房。县里广播站的记者还为此来采访过我。
● ● ●
1990年4月,我认识了冉邦荣。他和他哥哥,还有两个老表,从湖南龙山来到建始,在县城开了几个铺子卖服装。他们分了工,两个人守铺子做生意,两个人跑乡里。冉邦荣跑茅田、长梁这一带,和我一样,骑个摩托车。我也是跑江湖的,知道在外面跑不容易,又和他谈得来,便让他住在我家里。贺月华也乐意他在我们家落脚,住宿吃饭的钱算得清清楚楚,他不抠,出手大方。关键是他们在城里做生意,进的衣服款式新潮,虽然因为价格高,在乡里不好卖,但贺月华喜欢,他时不时就送件衣服给她。
他们生意做得不太好,城里的铺子赚不到钱,跑乡里的稍微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个喜欢打牌,有时窝在屋里打上整整几天,铺子门都不开。
冉邦荣见我生意好,就要跟我学,嘴里总是喊我樊师傅樊师傅。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我让他跟我跑了几次。他小我五岁,见过世面,人也勤快,在我家什么家务都做,还帮我父亲洗脚,说要认我父亲当干爹。可他的生意还是做不起来,我帮他推销也不行。
后来我劝他回县城开铺子,简单些。他不搞,说回去也是打牌,跑乡里总还是能挣点钱。我也懒得再管他,我跑我的,他跑他的,生意各做各。
● ● ●
认识冉邦荣以后,他去我家吃住的时间比我还多。我出一趟门,一般要好些天才能回一次,他生意没我好,所以隔三差五就去我家。那年腊月我出了最后一趟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那天回的家。长工短工,腊月二十四满工,我们乡里腊月二十四以后就都开始玩,不搞事了。我把年货都办齐了带回去的。劳累一年了,准备好好休息几天,好好过个年。
回家之后没看见贺月华,父亲说她让冉邦荣送她回娘家住几天,过年的时候回来。我感到不对劲,正月初一就要回娘家拜年,这眼看要过年了还往娘家跑什么。我骑上摩托车就去找她,可她娘家人说她没回去。我连夜赶到建始县城,冉邦荣几兄弟在四化路开的铺子早就关门了,人毛都看不见一个。
我明白了,冉邦荣把贺月华拐跑了。
我第二天就从县城坐车,找了三四天才找到冉邦荣的老家。他哥哥说冉邦荣确实带了一个女人回来,但只过了一夜就走了,去了福建。至于福建具体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没老婆可养,我想把钱捐给国家
老婆被人拐跑,让我在村里出了个大洋相,有人同情,更多的人是在看笑话。父亲受的打击比我还大,气病了,在床上睡着,正月家里来客人拜年都起不来。过完年没几天,父亲就死了。他临死之前还在骂我,骂我没用,说一早就说了我们八字合不拢,那女人就是个祸水。
我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养老婆。到头来,钱在口袋里装着,老婆没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赌博,一个人吃饭,冲上天也只需要那么点钱。有人劝我,再找一个女人。再找女人的时候,要看准,要能过日子。(最新经典文章 www.imhuang.cc)
我后来遇到过几个女人,都闹得不大愉快,经历过这些事,就不再接近女人了。我心灰意冷了,也没心思再拼命挣钱,再说钱也没那么好挣了,乡村里的小商店越开越多。走乡串户的生意不做了,就在家里窝着。有人上门理发,我收五块钱,多一分都不要。附近有谁家搞建设,需要泥瓦工,我就去干几天,多少挣点。钱虽然没以前挣得多,但过生活足够。
2010年的时候,村干部看我孤单,就把我送到了茅田福利院。只住了两个月,我不放心几间房子空着,就回家了。
现在我身体垮了,连做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回福利院来住。回想这一辈子,还是这里的日子过得安稳,有吃有穿,有国家养着。我给任院长交待了,哪天我死了,就帮我把存款捐给国家,把房子也卖了,钱捐给国家。
● ● ●
口述人:高焱明
男,1944年生,鄂州市梁子湖太和镇高梅村人
民间古板书表演艺人
1998年入住太和镇福利院
堤还没有做好,我的脚就受伤了
1977年,我三十三岁。生产队派任务,在涂镇湖做堤坝。晚谷割上岸就去了,做了一个多月了,堤还没有做好,脚就受伤了。那时候做什么都难,全靠人力。拖土用老式的两轮板车,两边竖起高高的墙板,一车土就有一千多斤,一个人根本降不住。因为是重事,大家就轮流做。那天本不是我拖土,可我们来的孩子太小了,还不到二十岁,根本拖不动板车。我看着心疼,就把他换下来,让他去锹土上车,我顶替他拖板车。
下午三四点的样子,我拖的板车突然翻了。我没有注意到,两个车轮底下一边是泡土,一边是大土墩。泡土那边,车轮空了,车子往一边倒。车把飞过来把我的腿刷断了。我疼得像杀猪一样大叫。大伙都停了下来,领导派了两个人把我抬到指挥部,其他人继续做事,毕竟生产进度比我的脚重要。
医护室只有张有秉一个赤脚医生,他没有真手艺,把我害惨了。实际上,是脚踝受伤,螺丝骨翘起来,把碗打破了。他非说是脚笼管断了,直接用两块杉树皮捆。无论我怎么喊痛,他也不怀疑是自己搞错了。
生产队派人用竹床抬我回家。我在上面哭着喊,让他们慢一点,慢一点,但他们还是走得很快。他们每走一步,我就哎哟一下,钻心痛。
抬回家后,姆妈看见我就哇哇哭。家里的主劳力受伤了,残废了,日子没法过了。再说,这一病肯定要花很多钱才能治好。姆妈的哭声比刀还狠,一声一声,刮着我的骨头。
家里没有钱,但还是想办法给我治疗,把我抬到毛家去找接骨的老医生,医生当时一摸就说接错了。他一说,我就哭了。
老医生当时阶级不好,不敢给人看病。我们找大队开了证明,他才答应下来。
生产队把我抬回家就不管了,我们只好借钱治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脚才不那么痛。一年多,镇上干部说好的工分都没给我。我的脚刚可以走路,就去找镇上的干部写了批条,生产队这才补给我钱和工分。
在床上躺了快两年,我们的那个小伙子,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听说涂镇湖现在破堤还湖了。
学会说书后,我风光过一阵子
1980年,分田到户了。各家各户干自己的农活,我却动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想死的心都有。以前是政策不好,阶级成分不好,三十多了还没有成家,现在政策好了,我却瘫了。
后来,我们来了说书的。家人为了让我散心,就把我背去听。结果,奇迹出现了。
说书人见了我,立马走下台来打招呼。我们是老熟人,我听过他说书,还当场指出过他的破绽。我喜欢看故事书,他说的内容,我都晓得,所以能听出他是不是说对了。他见我的脚这样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想学说书,让他教我。他说教不了——我的故事讲得比他好,又捅过他的娄子,而且他也怕教会了我,会抢他的饭碗。
于是,我让他只教我打鼓,打着好玩。他答应了。但我没有鼓,他就教我练空动作。他估计我嫌躺在床上烦,敲敲打打的好打发日子,过去了就会放弃。但没有想到,我捏着筷子在桌子上击打,右手捏棍子,左手晃动大拇指,这样练了两个多月,还真的就学会了。更奇怪的是,学会了敲鼓板,我的脚也消肿了。后来,父亲用两块钱给我买回来一个破鼓。
有了破鼓我就开始说书了。我的第一场演出是在梁子镇高家嘴。当时我有点害怕,就挑了家门口。可哪知道,我天生是说书的料,一上台就什么都忘了,只有心里的故事。那一次,在高家嘴说了七个晚上《秦琼卖马》,连续七个晚上,得了十四元钱。每天还有一包烟,游泳牌的。
● ● ●
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八十年代初,还没有电视,里要是来了个说书的,就会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各家各户把三亲六眷都接来做客,听书。而我则享受贵宾待遇,每天一包烟不说,队长还会特意去各家做工作,派到谁家接待,就要拿出最好的饭菜。我不喜欢吃肉,就让他们给炖碗鱼汤,或者黄颡鱼鲶鱼下面条。梁子湖边上,鱼虽然是贵东西,但总比肉好找一些,便宜一些。那时候,谁家里都过得不宽裕。主家知道我这是体谅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饱饱地吃过晚饭,我就端了茶杯去说书。说书的场子一般是在村的禾场或者是祠堂。一桌一椅一鼓,我的道具就这么多。看底下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惊堂木一拍,开讲。
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人长得好,一米八的个子,三十刚出头,英气逼人。说书的时候,邪头怪脑的,讲到精彩的地方,他们不光是竖起耳朵听,还会笑得拍巴掌,前翻后仰的也有。
说书的日子有吃的有抽的,又不累,颇有滋味。
那些年我就像个明星,只要背着鼓板,在路上走,就会有人追着我赶。把我拦着,让我去他们的开场子。有时候,刚在这个子开场,其他的子就有人来预定,还没等说完,鼓板就被人接走了。
我不想作恶,所以错过姻缘
说书的时候,人心情好,春风满面,容易招惹桃花。沼山镇孙胡谈有个叫欢子的细女娃,总是坐到最前排,竖起耳朵听,一场都不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在他们说书的那几天,欢子总是跟着我。我去湖边洗衣裳,她也跟着。还带着我走蛮远,说那边的水更好。黄昏,太阳快要沉到水里去了。欢子一路跟着我说说笑笑,长长的辫子,白白的皮肤,嘴唇红艳艳的,真好看。说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欢子偷偷和我说,明天到长岭街上等我。她是想和我私奔了。
那一晚上我没有睡好,恍恍惚惚的,总做梦。在梦里,欢子的家人追着我们赶,吓得我醒来后还出一身冷汗。第二天,我起晚了。正犹豫着要不要和欢子碰面,就被张家五房的人拦住了,他们要我去开场子。生意来了不能不做,再说,去长岭还不知道是福是祸。我就跟他们走了。后来听说,欢子那天在长岭街哭得好厉害。
沼山镇洪内村有个叫蛾子的姑娘,十六岁,也喜欢听我说书。在他们说书结束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出工,跑到我睡的房里,把门闩上了,也不说话。在房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眼睛总往我身上瞟。我假装睡着了,我知道她想做么事,但我不能那样做。我眼睛闭得紧紧的,可心儿怦怦跳,如果我不用手摁住,它就会蹦出来似的。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娥子带着包袱,在山口等我。说要跟我回家。我就骂她,你一个姑娘家家怎么可以跟男人跑。我让她赶紧回家去照顾她的妈妈。
那么多女孩喜欢我,但最后我还是一个老婆都没有。那时,我才刚开始说书,没有存到钱,而且我又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的。我不敢做坏事,万一她们反咬我一口,告我拐带妇女,那就糟了。
我的师傅,就是那个教我敲鼓板的师傅,他就是在说书的时候和别人好,被人打个半死。他说了一辈子书,没有结婚,前几年在福利院去世。
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保长,之后因为这,我们家被划定为“四类分子”家庭。带了帽子,那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时不时就把我父亲支出去挖地洞。红卫兵一来,把家里的东西一气乱打,坛坛罐罐的碎一地,你还不能气,不能和他们对着来,不能反抗。要忍着,你不知道,要是反抗了,我父亲会遭更多的罪。
我的脾气就是这样被冤没了的。
● ● ●
后来政策慢慢好了,“帽子”随风吹了,我的头也就伸出来了。
我三十六的时候,在保安镇说书碰到的一个女人,女人长得眉目清秀,但就是眉头一直紧锁。后来,轮到她家接待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老公是个病秧子。女人的日子过得很紧巴,但接待的饭菜还是很丰盛,这让我突然很动心,就提出要和他家结拜亲家,也就是说让她的孩子认我做干老子。那是当着他老公的面结的亲戚。后来来往多了,就和她好上了。我心疼她,想帮她。她说要离婚跟我,我没有同意。我还是到处去说书,隔一段时间就带着钱去她家。那几年,我帮她建了一栋房子,还帮她治好了她丈夫的病。
她丈夫肯定知道我们的事儿,以前从来不提,等病好了,就介意了,还打了女人。我提出要带女人走,结果,她不肯离婚。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去找她了。
四十八岁的时候,我又有了一个女人,没有拿结婚证,但她在我家里住了大半年。她是被人带到太和来的崇阳婆子,肚子蛮大,一看就晓得是有病。我看她蛮作孽的,就从介绍人那里把她带回家了。
那时候我的心思都在牌桌上,每天都往太和街跑,街上有大牌铺,时时刻刻有牌打。我白天打牌,晚上说书。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电视了,但到了晚上,他们还是喜欢到大院子里坐在一起诳天。我给他们说书,他们这个给一块,那个给五块,一个晚上下来,最高的时候可以有一百多元钱的收入。收工后,再去下个馆子抿几盅小酒,日子过得潇洒着呢。
家里的崇阳婆子其实蛮好的,只要我把柴米油盐弄到家里来,她基本上不管我。我还给她治病,把她的大肚子治好了。她也好,每年给我养几头猪。但我不能真心对她好,因为她总是牵挂她在崇阳的孩子。我就知道她的心不在这里。
后来,我们有个人跑来告诉我,你屋里的婶子走了。我知道她是要走的。我跑回家去看我的钱,她没有多拿,就拿了几十元钱,大概是做车费。另外,我看到猪食已经煮好了,水缸也挑满了。
我知道她的心里欠着娃。她是应该回崇阳去的。
来源:女娲之爱 love.ngnvip.com 口述实录 love.ngnvip.com/category/koushush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