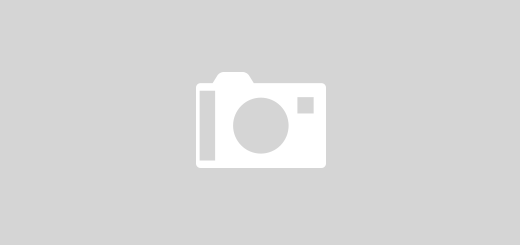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58年,我们始终相亲相爱……
丈夫:闵召连
年龄:79岁
职业:退休干部
妻子:朱遵兰
年龄:78岁
职业:退休工人
时间:10月18日
地点:永安街道建南社区
记录整理:灯火阑珊
摄影:秦媛
深秋,一个暖融融的午后,我来到永安街道建南社区的徐州矿务集团家属大院。叩响了退休干部闵召连老先生的家,他和老伴朱遵兰阿姨乐呵呵地接待了我。两位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走进闵老家不大的客厅,他们鹤发童颜的婚纱照映入眼帘。瞧,他们相互依偎着,那微笑中透着满足和幸福。刚刚落座,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告诉我,10月18日恰是他们结婚58周年的纪念日。于是,我们的话题便从58年前俩老人一见倾心说起。
闵召连:母亲做了我的求爱信使
淮海战役的硝烟在徐州还没完全散尽,为了保卫矿山的安全,使其生产正常进行。我应招成为了一名预备役,到了贾汪区的夏桥煤矿,做安保工作。
我是1949年到那里工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几年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这期间也不乏有年轻貌美的姑娘,含蓄地表达对我的倾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受,也许感觉自己与她们不够那份缘吧,似乎我在等待着自己真正缘分的出现。
那么我命中缘分的她在哪里呢?直到1953年,我回家探亲见到她(闵老指了指坐在身边的朱阿姨),我这心里才有了目标。
我16岁便应招离开家,由于我工作的特殊性,虽然夏桥煤矿距离我们村庄不是那么远,我却很少回家探亲,全心全意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中。保卫任务一个接一个,那时候也是年轻,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1953年的夏天,我终于回家探亲了。我家人口多,我们兄弟7个,老老少少看到我回家了,都特别高兴。一个大家庭热热闹闹吃过饭,我就想去看看我多年不见的一位同窗好友。
他姓朱,住在我们村庄的最南端,而我们家则住在庄子的最北面。久违的好友自然相谈甚欢,这期间我见到了他的妹妹兰,多年前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几年不见,就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间还透着姑娘家特有的灵气。虽然穿戴陈旧,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她礼貌地朝我羞涩地笑笑,我的眼前一亮。我和她哥哥继续坐在院子的大树下攀谈,直到月上中天我才告辞。
回家的路上,我独自走在田间的小路上。不知道是见到老同学谈话谈兴奋了,还是因为见到了已长成大姑娘的兰,反正心中莫名的兴奋。我朝家的方向慢慢地踱着,挥之不去的尽是兰的影子。想着想着我心中的“目标”,就这样确立了。那时候年轻,这目标一出现,心底便不由自主地畅想起来。田间的夏虫叫声也显得十分悦耳,似乎在为我确立的目标而歌唱。
我回到家已近子夜,母亲没有休息还在等我。平时我有啥事总爱和母亲说说,这么大的事我当然要告诉她喽。因为都在一个村里,我想母亲对她以及她家还是了解一些的。所以我就将想娶她的心思告诉了母亲,我注意到她老人家一直笑着听我讲,我知道这就说明她是同意的。
第二天我给兰写了一封信,含蓄表达了我对她的倾慕之情。信写好了,可是谁来做我的信使呢?为此我还纠结半天。最后我回单位之前,把信交予了母亲,请她把信送过去,母亲接过信笑笑地看着我啥也没说。
闵召连:没费任何周折就把她娶回家
我回到单位大约一周的时间,兰的母亲带着她来矿上找我。我非常意外,当然也很高兴。当时我大哥家就在矿上,我对哥嫂一说这情况,他们便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女,我带她们在矿上各处参观参观,那天她们就住在我哥嫂家。
第二天,她娘俩笑眯眯地坐车回老家了。我知道她妈妈是来矿上考察我的,瞧见她们的笑容,我心想,娶她是八九不离十了。之后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特想见她,心里总在盘算着回家。可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回家的打算只能在心中盘旋着。我们常常通过来去的亲戚、邻居捎个口信来表示彼此的惦念。这时家里不断传来为我筹备婚礼的消息。
1953年国庆节后,我终于有了假期。那时结婚登记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我是揣着介绍信离开矿上的。回到家一看两家老人已经做好了婚嫁的准备,只欠我这个“东风”。我自然喜不自禁,于是放下行李就和家人一起做着最后的准备。
10月18日,是我永远都会记着的一天,我们去办理结婚登记。说来不可思议,那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向登记机关的。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是沿着铁轨一起走的,而且我们不好意思肩并肩地走:我走在铁轨的右侧,而她却低着头走在铁轨的左侧。登完记没有几天,家人为我们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喇叭声声,鞭炮震天响,似乎整个庄子都在办婚礼。
朱遵兰:牵了手的手路不一定好走
俺俩举行过婚礼没几天,闵召连的假期就结束了。他带着我一起回矿上,从此我就脱离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那时没多想,只知道嫁给了他就该随他去。矿上生活区有几排低矮的平房,每一间大约有10平方左右,我们也和其他新结婚的小夫妻一样分得了一间。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好的,我也很满足。
回到岗位,他依然很忙。忙的我往往许多天都见到他,一出差时就会很久。那时他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每个月领到工资就要先给双方家里一些,这样虽然我们的生活有些拮据,但我们感觉那是理所应当的。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在矿上做起了家属工,我先后做过托砖坯、编八片、装卸工,煤车一来我们就抄起大铁锨往车上装煤矸石,当时我只有80多斤,而一铁锨煤矸石是20多斤。我还在食堂摊过煎饼,一个人要看两个大鏊子。这时我已经生过大孩子,还要自己带孩子。我把几个月的孩子带到岗位上,放在一个自己做的大“摇篮”里,孩子哭了我就用脚蹬两下摇篮。手却还在两个鏊子间操作着,一摞摞香喷喷的煎饼就这样烙出来了。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工作生活真够艰苦的,可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再苦再累都毫无怨言,觉得生活原本如此。当每一个月我领到25块钱时,心里还是很开心的,这毕竟是我劳动所得。
我揣着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婆婆早已从老家来到了我家,我赶忙做饭招待她。把最好的细米白面拿出来给她吃,做好了往往要去请多次她才上桌,我不急更不生气,婆婆嘛,理应摆摆架子。第二天她就要回老家,我再递上几块钱。
后来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后,生活更加窘迫。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春天我爬到树上采榆树钱晒干磨成面充粮,秋天我去田里捞地瓜……其实在那个缺粮少油的年月里,挨饿似乎不足为奇。我却总有办法“变出”充饥的东西来,一家人从未挨过饿。
我们的孩子也并不觉得苦,他们从小都很懂事,帮着我捡煤干活。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是他们的爸爸出差回来,他出差在外,自己想方设法地省了又省,把节余下来的粮票和钱给孩子们买来上海、广州的糕点,在那些经济极度匮乏时期,一块小饼干都是奢侈品。
<p
闵召连:
幸福着我们的幸福
现在好了,超市里各地的糕点、水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是苦了她了,我经常出差在外,就是不出差也是忙得不着家。4个孩子我是没有付出多少,全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她不仅支撑着这个家,还一天不落地在矿上做那些很艰苦的工作,从没有过怨言,任劳任怨地一如既往。
倒是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我,说我都是办公室主任了,怎么也该给嫂子换个岗位转转正。其实我不是没有想过给她改变一下环境,但觉得自己是干部,这样做不妥,所以一直到1977年,她们那些家属工全部转的时候,她才转成正式工。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喜欢养花种树,院内院外我种植了枣树、石榴等树木。我还养了各类的盆花,那时候我们的小院里、房里房上到处的鲜花,最多的时候仅月季花我就养了三百多个品种。期间我买回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还为花儿们做了卡片。我退休后就更有时间侍弄它们,直到那年我患病住进了医院。病愈出院感觉体力不支,才忍痛割爱,将花一盆盆送给老朋友。
而今虽然没有花草的陪伴,却有孝顺的儿女们体贴我。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我们家的媳妇、女婿在别人眼里就像是女儿、儿子。他们在岗位上积极努力,在家里勤恳节俭,对孩子严格要求。如今孙辈们大都有所成绩,大都考入了高校。有的在高校任教,还有在外省省工会工作。
平时儿女、孙辈都很忙,一到节假日,孩子们便会像候鸟回“巢”一样纷纷聚来,那是我们最为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每一次我们这个近20口人的大家庭都是到酒店聚餐,孩子们喜笑颜开,拥着我们走进酒店,常常扯来好多羡慕的眼光,真没有想到老年的我们会有这样好的日子。
(文中人物均为真实姓名)
■采访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闵老先生说的最多的就是:“没想到我们现在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
二老的经历是平凡的,而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他们牵手走过艰苦的岁月,却从不言难,只是淡淡地聊着过程、聊着面对。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目的地的旅行,只要你不忘记旅行的意义,你就会享受这样一次旅行,而不被种种羁绊所困扰。也许闵老先生深谙其道,所以他说起老伴对家的付出总是充满了感激,对现在生活是那么的满足。
来源:女娲之爱 love.ngnvip.com 口述实录 love.ngnvip.com/category/koushush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