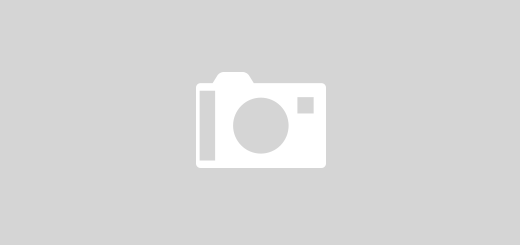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我用一生祭奠我的悲情初恋……
被采访人:宜民
性别:男
年龄:56岁
职业:某乐团作曲兼指挥
学历:大学
采访时间:2004年8月
采访地点:某乐团
采访人:陈宏光
我们用二胡曲作暗号
绝没有想到初恋会影响我的一生。
她是我读艺校时的小师妹,姓叶,同学们都叫她叶子。我也叫她叶子,不过我呼唤叶子的感觉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她是神圣爱情的一片永远的新绿。
我读艺校是迫不得已的事。初中在北京四中就读,按我的成绩,本应当顺利考进一所名牌大学的。但是,母亲靠做临时工的微薄收入抚养我,生活实在太艰难了。1964年,我自作主张放弃了已被高中录取的母校四中,放弃了想当一名核物理学家的崇高理想,凭着自己会拉一手二胡的小小特长,考取了这所管吃管住的艺术类中专学校。认识了叶子,或许是命运给我的一个回报吧。
艺校的主科是戏曲,我在音乐科学二胡,叶子在表演科修京剧,我们本没有什么缘分。然而,至今我都回忆不清楚,到底在什么场合我俩熟悉起来的。总之,入校不久,她就出现在我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文化课的功底好,叶子从小学戏文化底子差,总是找我问功课;也许是我生活太懒散,衣裳、被子都不会洗,热心的叶子总是帮我洗衣服。反正没几个月我俩便无话不谈了。以前,我对戏曲知之甚少,从叶子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长生殿》、《柳荫记》、《西厢记》这批名剧的剧情;而我给叶子讲述《苔丝》、《基督山伯爵》、《红字》等外国名著时,也常让叶子听得如醉如痴。那一段日子,太纯真了,太令人留恋了。我俩常来常往,没有顾忌,她叫我民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超出师兄妹的丝毫念头。
人生的幸与不幸永远是捉摸不定的。
1965年深秋的某日,叶子忽然约我到陶然亭公园去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还奇怪,什么事在学校不能说,非要去公园呢?
那晚,秋风萧瑟,陶然亭遍地落叶。我如约来到北门那座石桥边,却突然惊见叶子伏在桥栏上啜泣。我问了几句她都不抬头,弄得我心里慌慌的。这时,她猛地仰起脸,用噙满泪水的双眸望着我,声音嘶哑地问:“民哥,别瞒我,你家到底是什么出身?”
我愣了。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敏感问题。
我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听母亲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级别还挺高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在押,并且没关在北京。于是,我如实把这些情况对叶子讲了。
原来,艺校正在发展团员,叶子是工人家庭,根红苗正,专业条件又好,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却成了她入团的障碍。年级政治辅导员明确对她讲,要入团可以,必须先和“反动家庭”出身的我划清界限。
此后,我们结束了一切公开交往,在人前装成陌生人一样,但心里却真正地爱上了她。音乐成了我们沟通的暗号。我编了一批二胡短曲,包括“祝你考试顺利”、“今晚老地方见”、“有急事外出”等,曲调只有我俩熟知。有事时,我在宿舍楼道拉两遍,住在二楼的叶子立刻明了。谁能想到,如今被人称为作曲家的我,第一次作曲竟会是为了初恋。1966年8月7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政治辅导员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两位民警。民警说,宜民,你母亲抗拒红卫兵“破四旧”被打伤了,已经快不行了,你回家料理后事吧。我像被雷击一般,浑身发颤,疯了似的冲出办公室,回宿舍用二胡狂拉了两句“急事”曲调,便朝自己家奔去。我家的小屋一片狼藉,母亲伤痕累累地斜卧在床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外一个身影哭叫着扑到母亲的床边。竟是叶子赶到了。不知是什么神奇力量的驱使,叶子的哭声使弥留之际的母亲又睁开了眼。我和叶子赶紧围上去,老人挣扎一通,说不出话来,却从怀里摸出一只银手镯,抖抖地戴在了叶子的手腕上。母亲望了叶子片刻,喉咙咕噜一声响便咽了气。叶子悲怆地喊出了一声“妈!”
我俩双双跪在母亲的床前。那年,都18岁。
听说我还活着,她当时就昏倒了
1967年,我们毕业了。大约我和叶子的关系隐藏得比较好,没有影响到她的毕业分配。她被一个部队文艺团体相中,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我的分配比较离奇,说是查出我“反动父母”原籍山西,便把我分配到山西一个偏远山区的县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离别那天,我俩相约来到陶然亭,湖边坐了许久,却又相对无言。天各一方已是事实,未来希望更是无从知晓。叶子反复只是一句话:“我等你。”从此一别天涯。
刚到山西那几个月,我还可以和叶子通信,后来状况却急转直下。在小地方我成了被批斗的重点人物。有一阵,我绝望了,以死抗争,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把我放到当地一生产队监督劳动。等到我稍有自由时,再给叶子写信,却被退回,信封批注是“地址有误”。几年后,我才有机会回了趟北京,却听到了叶子已经结婚的消息。
同学告诉我,我去山西没半年,便传来“宜民畏罪自杀”的消息。叶子哭了几天,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得来的结果仍是我已“畏罪自杀”。
她等了我三年,她所在部队一个连长追求了她三年。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嫁给了那个连长。当我又活着重新出现在北京,有同学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当时就昏倒了,醒来后只是木然地说:“我命苦哇。”
在老同学的安排下,我和叶子见了面,有了第一次的相拥而泣。我让她离婚跟我走,叶子对我说:“民哥,我不能让你再犯’破坏军婚’的罪。我的心永远是你的,你明白就行了。”
悄悄地恢复了通信,但真情却被现实阻隔。1978年,我凭借勤奋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而叶子却随丈夫一起转业回了东北老家。她来信说,她被安排在县蔬菜公司卖菜。
大学四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从东北小县城寄来的包裹或汇款单,我怎样劝说也阻止不了。叶子在行信中说:“你没有亲人,全当我是你的亲妹妹,我定会供你完成学业,在音乐天地里施展你的才华。”
后来我才听说,其实,叶子回东北后风吹日晒地卖菜,早已没有了当女演员时的姣好容颜。而我在毕业后已回北京进了乐团。想起她为我做的一切,我躲在宿舍里任泪水流淌……
十多年的相思之苦哇,我却无以回报。
<p
她寄回了妈妈临终前送的那只手镯
1988年初春,我创作的第一部以二胡独奏为主旋律的民乐组曲《春之思》公演。演出前,我便兴奋地写信告诉叶子:“这可能是我毕生最值得纪念的作品。”
演出那天,我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琴弦上,乐团同仁也受了感染,演奏情绪非常到位,每个乐章都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但演奏到第二乐章时,观众席曾有过一阵骚动,片刻就过去了。间隙时,同事告诉我,有个观众昏倒了,已经被人抬出剧场。
演出结束,我的一位艺校的老同学匆匆跑到后台找我。劈头就一句:“宜民,刚才叶子昏倒在剧场,你快跟我去看看她吧!”我顿时热血沸腾,抓住老同学的手,大声喊:“她来北京了?为什么不告诉我?”老同学回答:“叶子让瞒着你的,怕影响你的首演。她现在珠市口一家小旅馆里。”
终于又见到叶子,我感到恍若隔世。叶子躺在小旅馆的床上,面容憔悴,见我进来,挣扎着坐起来,激动地说:“民哥,我听懂了,你的音乐里有’祝你考试顺利’,有’今晚老地方见’……”我也动情地说:“不错,叶子,这部作品就是为你写的,它是青春的见证。”
在场的几个老同学都知情,人人落了泪。那晚,我们这群老同学通宵未眠,在小旅馆回忆过去,畅谈未来。他们指着我和叶子说:“你们的缘分有盼头了。” 第二天,叶子执意要回东北,说家里离不开她,我们相聚来日方长。
这次分手半年后,我收到了从东北寄来的一个小包裹,打开后,是那只妈妈临终前送给叶子的银手镯。
我赶紧给叶子写信问她为什么要把手镯寄回来。
可信刚寄出就传来了噩耗,叶子已逝,死于癌症。
杨易谈情
灰色背景下的亮丽爱情
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制造了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我相信,这类故事一定不止一个。而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年代有点久远的爱情故事,不是猎奇,而是希望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读完故事,我的脑子里一直跳动的字眼是“悲怆”、“圣洁”、“相知”等美丽的字眼。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在一段灰色的背景下更见它的光辉。我在想,尽管故事的女主人公苦恋了一生,直至英年早逝,但我想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幸福着的,因为她相信尽管他们相距遥远,但他们是爱着的。
与他们比起来,现代的某些爱情悲剧却让人觉得无谓与无聊。有些夫妻或恋人,成天生活在欺骗、谎言、猜忌里,我想这些消极的东西对人的折磨也许更让人意志消沉。所以,想想叶子和宜民,我们似乎该说:千万别放着好日子不过!
编辑推荐:小三,我把老公拱手让给你出轨妻子红着脸打开房门我给老婆的情人戴上绿帽子
来源:女娲之爱 love.ngnvip.com 口述实录 love.ngnvip.com/category/koushushi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