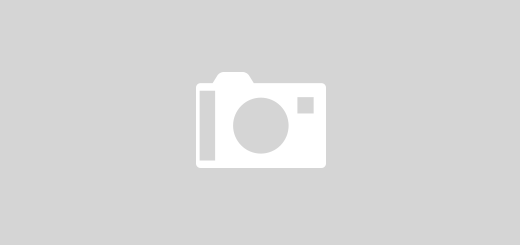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爱情小文章:绑住双腿玩弄花蒂,撕开她的乳罩慢慢揉捏……
他的身影从浓雾中浮现,从山坡下看,与同行的二人就像三抹行走的影子。天下着牛毛雨,昨夜的闷热像野兽被驱赶,转化成了散发腐烂味的湿热。鹭鸶和白鹭的振翅声愈发迟缓,从坡上远望,一对对橘色长腿在山下的水田里悠闲地蹚水。
鸟儿是从海角城的方向来的。
海风被一堆堆小山丘阻隔。白雾从湿漉漉的泥地和灌木丛中升起,好似海边离开岩穴的白色鸟群,鼓翼追逐天空的乌云。午后的三点暗得像傍晚的六点。草木集体沉默,树林里只有飘渺虚幻的雨声在不停地吟唱。
大地和他们的布鞋都喝饱了水。远处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灯光齐齐亮着。大山在阴影中静静等候被阳光启封。
他们于雨中身背双管猎枪在树林里漫步。
“你确定这条路是通往那棵榕树吗?”他处于三人的最后头,从晌午起,他们就冒雨上路离开了村子,背着枪寻找它的下落;蟋蟀伴着流水声在欢快地唱歌,他们被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飞蚊,水蛭,赶也赶不走。最前头的胖子和瘦子弯下腰撸起了裤管,在他之前涉入了水中。“如果不是为了村子,”他艰难地下蹲,随后双脚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谁愿意冒这样的辛苦,上山找这怪力乱神的东西呢。下不完的大雨,”他心里想,“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她才走了八天后,就让我的老腿受这种老罪。”
风雨声,像一个老花旦边唱边在繁叶间款款而行,一个又一个小时地行路让他感到头晕目眩;耳边,满是疾风在繁枝茂叶间回荡呻吟的声音。
他们一路摸爬而来,很是狼狈,领头的那个胖子回头说:
“我们就快到了。”
尾随的二人微微地抬起头,眼神与胖子短暂地碰上。黑白画册般的图景,三人在一片竹林里手持小刀,艰难地开辟着可行的小径。拦路的树枝被他们横刀砍断,竹子上,冰冷的雨水像青竹蛇从高处往低处盘绕而下,他手抓着竹干小心地下着坡,心里又不停地回忆起铺在前堂的那大块白布。“如果,”他又开始想,“如果她没有走,是不是这场雨根本就不会下。仔细想想,雨就是从她走了的那天下起的。首先它终结了酷夏,闭上了庄稼田里土地大张的嘴巴,那些开裂的土块是那么吓人。我原以为院子里的仙人掌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可是雨一下,一切又不同了。它喂饱了一切。起初如此,头三天,凉风伴着细雨,那感觉就像在海角城的港口坐船去大陆,摇晃的船舱黑暗且朦胧,如做梦一般。可是很快,在她走了的第四天起,那些原先干硬的地面就变得像泥鳅一样滑溜,路边的番石榴都被打下了枝头,头一天看起来笑呵呵的野花,也被淋成了一幅蔫了吧唧的模样。从第四天起,一切就像撞上大浪的小船失控了。第七天,傍晚村长来找我,身后跟着两个人,说:
‘这两个人知道怎么去找那棵榕树,你拾掇一下,明天准备和他们一起上路吧。’
他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是为这场止不住的大雨来的:
‘你真的相信老一辈人说的吗?关于那三只猴子。’
‘我不信,可如今只能信。’
我默不作声。说完,他们就转身离开了我家院子。我抬头看了看黑云遍布的天空,然后就进到屋子里找起我的猎枪来。”
“所以,这就是你要交代的一切了。”
“警官,应该说,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我们上了路,费了老大的劲,找到了那棵最大的榕树,然后布好了诱饵,在一处树丛后藏了起来,再然后第一只猴子就出现了,它中了陷阱,被我们布置好的绳网吊了起来。而猎枪是为了在林子里遇到云豹,迫不得已时才用的。”
“你刚才说的在你们村子的传说里,要抓三只猴子。这之后你们又等了下去?”
“嗯。我们抓到了第一只,按照先人们的说法,只有抓到第三只猴子才能消灾解难。”
“全是封建迷信!”
“我知道,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可是警官,你没种过田,你不知道,这场大雨让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你不曾梦到过那些稻子在梦里向我们诉苦,它们告诉我们它们就要淹死了,要我们救救它们,救救它们!”
“跨过这座小山丘,再走几铺路,前面就是那颗榕树。”
他们走出了竹林,又开始了爬坡。他觉得全身仿佛快要散架了,骨头行将作鸟兽散。但是没有,即便他已经不再年轻,一切都还是那么结实。眼前的芭蕉林里传来几声野鸭的啼叫,他们在一条窄道中穿行,脚下是粘稠的红泥土。巨大的芭蕉叶像雨伞阻隔着老天的眼泪,即便他身穿蓑衣,但全身早湿漉不已,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一刻不歇地行路着。
“我不该上路的,”他心想,“我不该答应村长。可我还是来了,女儿。离开你,去找祖先们说的那棵最大的榕树,为田里的庄稼寻找希望,为村子寻找希望,让这杀千刀的雨别再下。我还记得,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那是你十三岁的时候,那天也在下雨。我去你的学校接你,那天人很多,五颜六色的雨伞雨衣让我无法分辨,可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你和另一个女孩正咯咯地笑成一团。你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我,跑过来抱住了我。当时家里新添了一架拖拉机,我开着它,载着你,在当年乡里新铺的大路上,你告诉了我你数学考了上了九十分。你笑得像朵向日葵,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你告诉我你六年级的数学从未上过九十分。爸爸记得,所以我答应给你奖励,你知道吗?老天你知道吗?听我说完后她真的像个野孩子,你竟然跳到了路边别人家的玉米田里,在雨里兴奋地跳起了舞(我还记得你小时候,为了去镇里学芭蕾在我身旁撒娇的模样),我当时真的被你吓到了,我吼了你,因为你竟然跳车。可是你知道吗?你当时的舞姿真的像只湖心的天鹅。而爸爸这一生只见过你这一只天鹅……”眼前的道路有着尽头,回忆却是一片找不到归途的平原。
“‘出来吃口饭吧。’
‘爸爸,有人玷污了我。’
‘你说过,我知道。无论如何,出来吃口饭吧。’
‘我可能怀了他的孩子,我只想吐。’
一道竹帘阻隔了房间与世界,里面是她游丝般的声音。黑漆漆的门洞里仿佛居住着一只孤单的幽灵。里面的声音改换了腔调:
‘你应该让我去报警的。应该去报警的,即便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天那么黑,我看不清他的脸,可你应该让我去报警的。’
‘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警官,这不是为了我的脸面,而是为了她的未来。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直至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上大学第一天给我发来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现在手里还有当时她拍的照片。她乖巧地把双手别在身后,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袖口呢,是她自己做的泡泡袖。她微笑着,露出她的虎牙和梨涡,身上背着那个她从初中起就背着的粉色书包。谁能想象照片里这个乖巧的女孩小时候是个爱撒娇又爱哭的野丫头呢。她怎样都好,对我来讲只要她快乐就行。可一个被玷污的女人要怎么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丈夫呢。”
只听见“嗖”的一声,伴随着一阵树叶晃动与吼叫声,一只猴子被头朝下吊了起来。这是第一只,之后还得再抓两只,他心里想,
得抓到第三只猴子才能保佑村子未来无灾无难,风调雨顺。他们又设了一个陷阱。他听着面前的两人闲聊,他们说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这三只猴子是绝对不能伤到的,它们都是土地爷的信徒。大雨开始大了,天上的黑云变得越来越低,它们逐渐汇聚,好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巴掌要将地面的一切压扁。“这件事发生在正午,那时候我在甘蔗园里砍甘蔗。因为再过几天镇里就要举办一场拜神活动,我想着要赶快多砍一些,在集市上把它们卖完。那时候某某某就那么摇摇晃晃来到了我的跟前。某某某身上一股酒味,他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我不想招惹他,就假装没看见有人在我前面。
‘我看见你女儿上吊了。’隔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响嗝。‘我去你家院子里抓蛐蛐的时候,看到你家竹帘被卷了起来,她就那么吊在一根绳子上。脚边是一只被踢倒的脚凳。’
随后他倒到我面前,像只癞蛤蟆扑在地上,他嚷嚷着,嘴里感觉满是口水。我被吓了一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盯着他双目紧闭的脸,我知道这件事大概确实是真的。于是我回了家,看到平日里像瀑布一样垂下来的竹帘被卷了起来。在那无边的黑暗里,她是那么耀眼……
“之后呢,之后就是她的尸体被我停在前堂,用一块白布盖着。女儿从此不再痛苦,父亲却背负起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重担。我现在快喘不过气来了,我老了,我不该答应村长来抓什么猴子的。为了村子的未来,对,我的女儿失去了未来,可我为什么要帮害她去死的村子寻找希望呢,我不该来的,我这个糟老头应该跟着她去死才对。”
雨依旧大如盆泼。雨声。画面变黑白。空镜:灰色的天空。镜头变远景。河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警局内。一盏煤油灯。环绕的飞蛾。
“这就是我能交代的一切了,警官。我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女儿被人强暴了,我不让她报警,断送了她的希望,我还帮着那个强奸、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我的村子,去寻找止住大雨的方法。有一个村里人强奸了她!所以我忍不住开了枪,对,我向我们抓到的第一只猴子开了枪,既然传说中说那三只猴子不能受伤,我就非开枪不可,什么狗屁传说,都是胡扯。我忍不下去,开了一枪,另外两个人先是像木头人一样楞了一会儿,随后像疯狗一样把我死死摁住。
“现在呢,我给你们警察莫名其妙地逮住了,被你们审问。你们像疯了一样逼我说出村子哪去了,村子哪去了。村子当然还在原地!或许你们这些腐败的警察,是打算把某桩凶杀案安在我头上,那当然可以,我也早就不想活了。可是问我村子去哪了!村里人去哪了!村子和村民当然还留在原地,难道它真会因为我向那只泼猴开了一枪,就原地消失?好了,我不想多说了,让法官判我死刑吧,我也是害死我女儿的凶手之一。除了她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老得像堆土坷垃,像堆垃圾。但愿下辈子,我能做她的儿子,为她做牛做马。”
白雾,又一次吞没了一切。雨,仍在淅淅地下。大山仍坐在它原来的位子,在黑影的笼罩里。林子不停传来鹧鸪的啼叫声,水田里的白鹭和鹭鸶像影子一样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万家灯火,村子凭空不见了,只留下数以万倾的荒田和数不尽的枯树,不见半点炊烟。
雨中,一只死猴的尸体被整齐地安放在地上,一群猕猴围着它龇牙咧嘴,嘴里发出模糊的嘟哝声。一个破旧的土地爷神龛被挂在树上,群猴像人一样,对它四肢着地,顶礼膜拜个不停……
他的身影从浓雾中浮现,从山坡下看,与同行的二人就像三抹行走的影子。天下着牛毛雨,昨夜的闷热像野兽被驱赶,转化成了散发腐烂味的湿热。鹭鸶和白鹭的振翅声愈发迟缓,从坡上远望,一对对橘色长腿在山下的水田里悠闲地蹚水。
鸟儿是从海角城的方向来的。
海风被一堆堆小山丘阻隔。白雾从湿漉漉的泥地和灌木丛中升起,好似海边离开岩穴的白色鸟群,鼓翼追逐天空的乌云。午后的三点暗得像傍晚的六点。草木集体沉默,树林里只有飘渺虚幻的雨声在不停地吟唱。
大地和他们的布鞋都喝饱了水。远处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灯光齐齐亮着。大山在阴影中静静等候被阳光启封。
他们于雨中身背双管猎枪在树林里漫步。
“你确定这条路是通往那棵榕树吗?”他处于三人的最后头,从晌午起,他们就冒雨上路离开了村子,背着枪寻找它的下落;蟋蟀伴着流水声在欢快地唱歌,他们被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飞蚊,水蛭,赶也赶不走。最前头的胖子和瘦子弯下腰撸起了裤管,在他之前涉入了水中。“如果不是为了村子,”他艰难地下蹲,随后双脚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谁愿意冒这样的辛苦,上山找这怪力乱神的东西呢。下不完的大雨,”他心里想,“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她才走了八天后,就让我的老腿受这种老罪。”
风雨声,像一个老花旦边唱边在繁叶间款款而行,一个又一个小时地行路让他感到头晕目眩;耳边,满是疾风在繁枝茂叶间回荡呻吟的声音。
他们一路摸爬而来,很是狼狈,领头的那个胖子回头说:
“我们就快到了。”
尾随的二人微微地抬起头,眼神与胖子短暂地碰上。黑白画册般的图景,三人在一片竹林里手持小刀,艰难地开辟着可行的小径。拦路的树枝被他们横刀砍断,竹子上,冰冷的雨水像青竹蛇从高处往低处盘绕而下,他手抓着竹干小心地下着坡,心里又不停地回忆起铺在前堂的那大块白布。“如果,”他又开始想,“如果她没有走,是不是这场雨根本就不会下。仔细想想,雨就是从她走了的那天下起的。首先它终结了酷夏,闭上了庄稼田里土地大张的嘴巴,那些开裂的土块是那么吓人。我原以为院子里的仙人掌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可是雨一下,一切又不同了。它喂饱了一切。起初如此,头三天,凉风伴着细雨,那感觉就像在海角城的港口坐船去大陆,摇晃的船舱黑暗且朦胧,如做梦一般。可是很快,在她走了的第四天起,那些原先干硬的地面就变得像泥鳅一样滑溜,路边的番石榴都被打下了枝头,头一天看起来笑呵呵的野花,也被淋成了一幅蔫了吧唧的模样。从第四天起,一切就像撞上大浪的小船失控了。第七天,傍晚村长来找我,身后跟着两个人,说:
‘这两个人知道怎么去找那棵榕树,你拾掇一下,明天准备和他们一起上路吧。’
他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是为这场止不住的大雨来的:
‘你真的相信老一辈人说的吗?关于那三只猴子。’
‘我不信,可如今只能信。’
我默不作声。说完,他们就转身离开了我家院子。我抬头看了看黑云遍布的天空,然后就进到屋子里找起我的猎枪来。”
“所以,这就是你要交代的一切了。”
“警官,应该说,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我们上了路,费了老大的劲,找到了那棵最大的榕树,然后布好了诱饵,在一处树丛后藏了起来,再然后第一只猴子就出现了,它中了陷阱,被我们布置好的绳网吊了起来。而猎枪是为了在林子里遇到云豹,迫不得已时才用的。”
“你刚才说的在你们村子的传说里,要抓三只猴子。这之后你们又等了下去?”
“嗯。我们抓到了第一只,按照先人们的说法,只有抓到第三只猴子才能消灾解难。”
“全是封建迷信!”
“我知道,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可是警官,你没种过田,你不知道,这场大雨让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你不曾梦到过那些稻子在梦里向我们诉苦,它们告诉我们它们就要淹死了,要我们救救它们,救救它们!”
“跨过这座小山丘,再走几铺路,前面就是那颗榕树。”
他们走出了竹林,又开始了爬坡。他觉得全身仿佛快要散架了,骨头行将作鸟兽散。但是没有,即便他已经不再年轻,一切都还是那么结实。眼前的芭蕉林里传来几声野鸭的啼叫,他们在一条窄道中穿行,脚下是粘稠的红泥土。巨大的芭蕉叶像雨伞阻隔着老天的眼泪,即便他身穿蓑衣,但全身早湿漉不已,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一刻不歇地行路着。
“我不该上路的,”他心想,“我不该答应村长。可我还是来了,女儿。离开你,去找祖先们说的那棵最大的榕树,为田里的庄稼寻找希望,为村子寻找希望,让这杀千刀的雨别再下。我还记得,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那是你十三岁的时候,那天也在下雨。我去你的学校接你,那天人很多,五颜六色的雨伞雨衣让我无法分辨,可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你和
另一个女孩正咯咯地笑成一团。你也是,一眼就看到了我,跑过来抱住了我。当时家里新添了一架拖拉机,我开着它,载着你,在当年乡里新铺的大路上,你告诉了我你数学考了上了九十分。你笑得像朵向日葵,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你告诉我你六年级的数学从未上过九十分。爸爸记得,所以我答应给你奖励,你知道吗?老天你知道吗?听我说完后她真的像个野孩子,你竟然跳到了路边别人家的玉米田里,在雨里兴奋地跳起了舞(我还记得你小时候,为了去镇里学芭蕾在我身旁撒娇的模样),我当时真的被你吓到了,我吼了你,因为你竟然跳车。可是你知道吗?你当时的舞姿真的像只湖心的天鹅。而爸爸这一生只见过你这一只天鹅……”眼前的道路有着尽头,回忆却是一片找不到归途的平原。
“‘出来吃口饭吧。’
‘爸爸,有人玷污了我。’
‘你说过,我知道。无论如何,出来吃口饭吧。’
‘我可能怀了他的孩子,我只想吐。’
一道竹帘阻隔了房间与世界,里面是她游丝般的声音。黑漆漆的门洞里仿佛居住着一只孤单的幽灵。里面的声音改换了腔调:
‘你应该让我去报警的。应该去报警的,即便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天那么黑,我看不清他的脸,可你应该让我去报警的。’
‘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警官,这不是为了我的脸面,而是为了她的未来。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直至今天,我仍然记得她上大学第一天给我发来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现在手里还有当时她拍的照片。她乖巧地把双手别在身后,身上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连衣裙,袖口呢,是她自己做的泡泡袖。她微笑着,露出她的虎牙和梨涡,身上背着那个她从初中起就背着的粉色书包。谁能想象照片里这个乖巧的女孩小时候是个爱撒娇又爱哭的野丫头呢。她怎样都好,对我来讲只要她快乐就行。可一个被玷污的女人要怎么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丈夫呢。”
只听见“嗖”的一声,伴随着一阵树叶晃动与吼叫声,一只猴子被头朝下吊了起来。这是第一只,之后还得再抓两只,他心里想,
得抓到第三只猴子才能保佑村子未来无灾无难,风调雨顺。他们又设了一个陷阱。他听着面前的两人闲聊,他们说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这三只猴子是绝对不能伤到的,它们都是土地爷的信徒。大雨开始大了,天上的黑云变得越来越低,它们逐渐汇聚,好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巴掌要将地面的一切压扁。“这件事发生在正午,那时候我在甘蔗园里砍甘蔗。因为再过几天镇里就要举办一场拜神活动,我想着要赶快多砍一些,在集市上把它们卖完。那时候某某某就那么摇摇晃晃来到了我的跟前。某某某身上一股酒味,他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我不想招惹他,就假装没看见有人在我前面。
‘我看见你女儿上吊了。’隔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响嗝。‘我去你家院子里抓蛐蛐的时候,看到你家竹帘被卷了起来,她就那么吊在一根绳子上。脚边是一只被踢倒的脚凳。’
随后他倒到我面前,像只癞蛤蟆扑在地上,他嚷嚷着,嘴里感觉满是口水。我被吓了一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盯着他双目紧闭的脸,我知道这件事大概确实是真的。于是我回了家,看到平日里像瀑布一样垂下来的竹帘被卷了起来。在那无边的黑暗里,她是那么耀眼……
“之后呢,之后就是她的尸体被我停在前堂,用一块白布盖着。女儿从此不再痛苦,父亲却背负起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重担。我现在快喘不过气来了,我老了,我不该答应村长来抓什么猴子的。为了村子的未来,对,我的女儿失去了未来,可我为什么要帮害她去死的村子寻找希望呢,我不该来的,我这个糟老头应该跟着她去死才对。”
雨依旧大如盆泼。雨声。画面变黑白。空镜:灰色的天空。镜头变远景。河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警局内。一盏煤油灯。环绕的飞蛾。
“这就是我能交代的一切了,警官。我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女儿被人强暴了,我不让她报警,断送了她的希望,我还帮着那个强奸、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我的村子,去寻找止住大雨的方法。有一个村里人强奸了她!所以我忍不住开了枪,对,我向我们抓到的第一只猴子开了枪,既然传说中说那三只猴子不能受伤,我就非开枪不可,什么狗屁传说,都是胡扯。我忍不下去,开了一枪,另外两个人先是像木头人一样楞了一会儿,随后像疯狗一样把我死死摁住。
“现在呢,我给你们警察莫名其妙地逮住了,被你们审问。你们像疯了一样逼我说出村子哪去了,村子哪去了。村子当然还在原地!或许你们这些腐败的警察,是打算把某桩凶杀案安在我头上,那当然可以,我也早就不想活了。可是问我村子去哪了!村里人去哪了!村子和村民当然还留在原地,难道它真会因为我向那只泼猴开了一枪,就原地消失?好了,我不想多说了,让法官判我死刑吧,我也是害死我女儿的凶手之一。除了她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老得像堆土坷垃,像堆垃圾。但愿下辈子,我能做她的儿子,为她做牛做马。”
白雾,又一次吞没了一切。雨,仍在淅淅地下。大山仍坐在它原来的位子,在黑影的笼罩里。林子不停传来鹧鸪的啼叫声,水田里的白鹭和鹭鸶像影子一样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万家灯火,村子凭空不见了,只留下数以万倾的荒田和数不尽的枯树,不见半点炊烟。
雨中,一只死猴的尸体被整齐地安放在地上,一群猕猴围着它龇牙咧嘴,嘴里发出模糊的嘟哝声。一个破旧的土地爷神龛被挂在树上,群猴像人一样,对它四肢着地,顶礼膜拜个不停……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men.ngnvip.com
文章来源:女娲之汉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