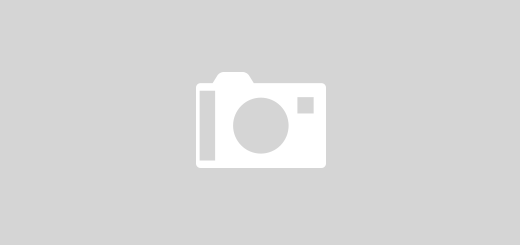女娲之汉|爱情小游戏:大叔你的太大了我难爱—第一次太紧进不去……
在须久那小时候,他参与过爷爷和一位被唤作“嘉瓦仁波切”的喇嘛的会晤。
彼时年仅四岁的他小小一团,跪坐在氆氇上,被眼前叮叮当当的银质茶器勾起兴趣,目不转睛地瞧使者用茶刀分割茯茶砖,再丢进锅里。加水,开火,火苗舔舐锅底,咕噜噜沸腾。红泥炉子的火安静燃烧,因故水才能沸腾,而当它达到一百度,必会停止升温,此时需将火灭掉了,否则水会蒸发殆尽,然而,停止加热,水便难以保持热度。细想想,这亦是一种因果的守恒。
使者将茶液滤净,倒入马嘴壶,又在净液中加酥油、牦牛奶和盐巴搅打。打好的酥油茶热酽酽地沏作五碗,第一碗抛洒于空敬天神,第二碗倒进炭火灭魔障,剩下三碗,毕恭毕敬地依此放到嘉瓦仁波切、爷爷和须久那的身前。
最后一碗的碗底提前搁有方糖,方糖遇热逐渐融化,使得茶液更稠。小孩捧起碗抿一口,果真稠挂糊嘴,滑糯赛蜜。爷爷和嘉瓦仁波切在翻译的帮助下正在交谈,须久那往炕火处挪了挪,兀自搛起块以肠网油包裹炙熟的牦牛肉吃将起来。
下一秒他吐了。这强烈的腥膻味他委实并不习惯,又嫌恶地嗅了嗅剩余部分,胡椒、肉蔻、小茴香在高温作用后显得酸涩焦苦,冲鼻难耐。他将它在茶水中涮了涮,丢到一旁。爷爷与身披红黄袈裟的嘉瓦仁波切,仍在谈论那幅内容可怕,却被作为礼物馈赠而来的老唐卡。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他们,还谈了什么。
壁火熊熊,柴木时而发出迸裂声。骷髅宝仗撬开恶鬼的獠牙,马头明王以忿怒相降伏三界魔障,金刚杵熠熠生辉,以其为意象的唐卡敬挂于壁炉上方,伴随回忆的话语声,须久那骇了一骇。室内昏暗,爷爷的眼睛被勾成两个黑魆魆的窟窿,火光幻灭无常。
今时今日,须久那终于自爷爷这里听来一番真话,又再一次看到了那副唐卡。他乍然忆起多年前那场会晤中更细节的内容。事实上,人对于年处四岁时未曾留意的事情,于九、十年后再冷不丁回忆,放一般者身上,那些只在意识中转瞬即逝的内容根本不可能被找回。然而好在,五条须久那不是一般者。他感觉有根针,将他自出生后生长到现在命里所发生的全部,都密密扎扎地穿缝作一串,甚至,还有些不属于他本人的记忆,都被针线缝了进来。
——是的,仁波切说,照您的意思来看,因德累斯顿石板而起的王权传承,和活佛转世有相似处。
——色即是空。一切事物都没有本质,可以说,只是暂时看起来,或在某种条件下会形成某种状态而已。“果”由各种“因”聚集在一起促合而成,“因”则是万变的,所以世间无常。这绝不意味着消极,相反,正因为无常,才赋予了人们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以达成改变,让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事不如愿或事事如意,都只是暂时性的,万事万物以变数发生波动,以无常作为常态,如若执着于相,陷入进去,才会生出痛苦。您以阴阳术数可以占卜到某种模糊的未来相,您已经预见到您孙儿的可能性以及他会逢遇伯乐的机缘命格,既然种种现象表明,黄金之王并非是他的伯乐,那么您不如稍安勿躁,静候佳缘。
——仁波切说,大成就者,不执于相。
你还记得那朵干瘪凋萎得徒留茎枝的花吗?——花车姑娘以无声的温柔将它送给流。姑娘的眼睛是紫色的。
花随海风翩扬,漂泊于浪沙,在天空打了一个又一个卷,告别云朵,终于落栖到溪水旁木屋的顶檐。须久那与它差了刚好半个手掌的距离,紫摘它下来。而后须久那将它送给了流,又将它扔进干藤蔓编就的垃圾筐。
光阴纾缓,我们必须承认,须久那搞错了一个步骤。彼时他尚不是懂得甄别的人,流望着他的眼神宁静且冷。幸好,他是那朵花,又不是那朵花。
这朵失去形状的花,它出生于温暖的玻璃房中,从未触碰过真正的自然,如今它要趟着雨水奔向未来,不知会被风刮去哪里,湍急的瀑布或冰冷的潭?缀满骆驼刺与红柳的大漠,或百万公顷的戈壁滩?然它早晚会随水流涌向大海,最终回到它来时的地方。
所以磐先生常年携带的那本黑皮书中记录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落,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转,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何处。
万物生发,冬季已往,时如浪涛。夏雨,止住过去了。
“假如色与空分离,且只能选择一个,你选什么?假如无相以流传与执相以灭失只能选一个,你选择什么?”
烟锅子在茶海沿磕了两磕。鎏金柄杆后端悬垂的翡翠鸾凤左摇右摆。
“家与国,战与和,因与果,你说说看,你又选什么?”
“亲情、爱欲、友谊,你说说看,为什么这些都和那块石板不能相比?”
大地裂开道缝隙,战争像瘟疫般迅速蔓延整个国家。波罗的海上空沉浮着燠热的风,夏潮湿而漫长,无边的漆黑的夜把一切都笼罩了,丛林纵深处偶尔传来鸟禽嘶鸣,依稀可以辨得蜘蛛网似的水域铺就在丛林外缘。成片的蕨类植物和鼠尾草生长在这里,此时却好像死了一样,随磅礴的雨颤动。
战火占领了德意志的内核,盘虬于内,即将吞并开外。帐篷一顶挨一顶,分布在水域旁。有谁跺了跺脚,跺去泥巴和雨,随后揭开帐篷的帘。青年嘟嘟囔囔地搁下丁字镐,脱下军装外套又使劲将其拧成个卷,水被攥出来渗进毡毯,变成一颗颗暗色的点。他走到炭盆旁,把皱皱巴巴的外套展平了搭上夹架,内衫仍因濡湿紧贴胸口,显得整个人污脏而狼狈。角落铺设的桌案后面,一个女人放下手中疾书的笔,摇了摇头,无奈地唤了声……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烟丝哔剥发亮,花果、香油、古柯混搅在一起的气味非常诡谲。命运以因果在三世流转,唐卡被壁火照映——马头明王是怙主观音以忿怒相在三界的化身——须久那被唐卡骇得失去形色,步步趋退,抵上墙面。
大地迎来了第一缕曙光。一些画面倏然间被熊熊壁火点燃,燃烧在他脑中,他尚不能搞清这到底怎么回事,唯能观想。然他觉得这种观想亦会令他窥见全然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一些沉淀已死的过往,被一点点灌进头颅,令他被迫过多汲取到不属于他的情绪和知觉,——不是吓唬人的,这非常恐怖,却是事实。就像他前段时间频繁所做的噩梦,和骨髓里隐隐作祟的某种激流一样,令他浑身颤栗。
爷爷在他到来后,未及他开口,便主动将过去之事轻予给他,紧接着又提出了四个大大的问题,尤令他僵涩不安。他踅寻不到答案,或者说不敢轻易做出选择。因为流说,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在他还不知道他能否为未来某个选择拿出相应的担当前,他不会轻易表态。
于是他盯住爷爷那张周正的怪脸,“我不需要回答您的怪问题,因为我到这里不是来为您答疑的。”扭扭脖子,步步趋近,“我感谢您,这一次您把有关于我的事,终于分毫不瞒我地尽数说了出来,谢谢谢谢,因为从前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此,亦证实了我某种猜想,嗯,原来黄金老怪和咱们家这么有缘么。”调侃地讲了两句,对面那两个黑窟窿下的胡须因这几句调侃而呼扇抖动,他感到一丝因凌驾对方而生的快感。
“不过可能得教您失望了,”他睨着他的祖父,房间中,祖孙二人形成某种对峙的气氛,使得原本的凝重变得更凝更重,“讲真,我不怎么在乎您说的事,也懒得和您聊我的听后感。下面我只简单说说我此次归家面见您的原因,我已经获知了绿之王比水流的关押地,就在学园岛,那么我近期定会展开营救行动,作为家族后人,此行危险重重,生死茫茫不定,故特来此通传,对,仅作通传,不作询问。为了五条家能延续香火,我劝您早作打算,安排我爸我妈再生一个,兴能让您在死前再抱个孙子呢,这回倍不准儿是无色。”
须久那整整领针,深吸一口气,“告辞。”话毕,他忽悠得转个身把背影抛给老者,扭开门把手,飞也似的逃离这个地方。
夏虫不可语冰。
他飞快地跑,顶着耶和华审判大地的吊顶,一圈又一圈地迈下旋梯,急促而慌张,似如不自量力的人类要逃离六道轮回的窠臼。最终,他跑到花园中西洋棋的雕塑前,栅栏陈旧锈蚀的门环围作一个圆。他掌着腿,在绿绒被中喘起粗气,双面因之前的紧张和后来的仓皇而涨满潮红。
面皮之下,有温暖的血在沸腾。外界不能停止对它加热,否则,它即要冷掉。须久那渴望力量,须久那渴望强权,可力量和强权背后,其所意味的真谛,怎能仅仅停留在孩童如此简单直白的渴望上?
色与空,无相以流传与执相以灭失,家与国,战与和,因与果,亲情、爱欲、友谊——为什么和那块石板不能相比。发问者在问谁,在问上一代黄金之王,还是在问迟了近十四年才成为黄金王储的五条后人。这些,流又知或不知,若知,知多少。
梦里花落。生与死在轮转,王的灵潜伏海底,亟待苏醒。明明知道逃不开命运的巨手,明明已经隐隐感觉甚乎接受了这点,却为什么在被告知真相后,仍愕然得像储君失了国土。
不不不,你失不了国土,放心吧你,已经拍定了,你就是国王。可如果你是国王,你就不能是五条须久那。你要选择“空”,你知众生无相,你的力量当为天下苍生流传,你有国,你必须主和,你不能沉浸于小我,未来,你要用你的全力去搭建一个可能性,一个最有利于众生的结果,之于你,自我、亲情、爱欲、友谊,加在一起,都不能再和那块破石头等量齐观。
要当个好王,拿起你的担当。而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在你错失且尚未赢回你深爱的那个人的今天。
你没有。
至少现在你没有,那你就不要轻易醒来。
可你不醒来,你又打不成美好的仗,你又不能以最精彩的战役,夺那个人回来。然即便你苏醒了,你仍想做个痴儿,让那个人来亲自教你如何做前面那些选择,教你怎么当个好王。
那个人是个好王。
空气黏腻,蝉如禅般孤寂,花儿打坐,一声鹤唳。庭院深深,鸟声如洗,铅华似锦。连廊飞檐外摇摆不定的光影,仿佛能将黑色大地上干与未干的血都漂洗了去。人间静默如诗。
——要摸摸,要抱抱,要啾啾。
快点让流回到我的身边罢,他这样想着,一点一点就着劲儿让自己立起来。浅色的发稍被汗水沁透,紧贴他的鬓颊。快点、快点让流回到我的身边罢,他还在重复这样想。
末了他发现,他果然仍是不自觉亦无可避免的,在心灵上依止着流。他甚至想把流的心脏从废墟中刨出来,拿刀子劈开,把自己填塞进去,缝合,再把这颗塞了五条须久那的心脏强行掖回流的胸膛。
即便,那里一定已先站了紫。
须久那掩着脸。
先来后到,这真是令人伤怀无奈却最终需得妥协的现实。
他越来越想揍紫了。没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一顿发个邪火再说,反正流会前场战役输给白银之王,与紫没杀夜刀神狗郎决计脱不开干系。宗像礼司是混蛋,白银之王是混蛋,夜刀神狗郎是混蛋,紫是个大混蛋。完后他想抢夺流,在这次事件结束后,未来和紫做光明正大的抢夺战。还有,他仅剩四余载便成年了,他想问流要成年礼,当然流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那时候流大概打不过他了?不过一切皆依托于某样时机的成熟,然后,再没有人能动摇他的位置。
啪。
须久那咣地甩了自己一个耳光。
畜生,想什么呢?!
你能耐啊,人都没弄出来呢,就忙不迭开始想后面该怎么整顿你五条须久那的小家了?——好吧,光靠想想来发泄发泄得了,立场在这里摆着,绝不能外面还没解决干净,倒先和紫窝里掐。须久那平静了一下心绪,整理了一下思维,掏出终端给紫拨去了电话。
紫敷面膜呢。头发上下系作两束,之后整合一束绾个团顶在后脑勺。鬓角的细伤,已全然愈合。
凤隐于林陌上寒烟笼半,宁可错,幽人在丘沙洲石楠一朵,这才落。御芍神紫是个世外神仙,他才不管尘世是否颠簸,有否小鬼撒泼打鼓,苍云白雾血染山河任教风马牛,在他的心里皆被染成透明。燕子停驻水边,一只鸟沉眠在他的心湖。
他就这么立在窗前望景,曦霞随风吹拂上面颊,琴坂支在他的肩头。这个画面我们有点熟悉,前一年他独身攻占御柱塔后,也是和这只绿鸟以这个姿势在窗前望景,细微的不同在于,当时他没穿居家服没敷面膜没绾头发且御柱塔是落地窗,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流在用琴坂和他聊天。
紫接起终端,语气悠悠,懒懒洋洋。“呐,如何?”
孩子不知置身何处,总归像是正捂着嘴讲话,声音听来瓮瓮瘪瘪,如被絮状粘液裹搅住了声带,让他的嗓音着实显得喑哑。我给你讲个故事,听么,紫,须久那问。紫以指背试着面膜的干湿度,静候对方弦外音。
五条须久那差点姓了国常路。
平安时代起,国常路一族便与五条一族共分神道界天下,五条家主知悉德累斯顿石板及王权体系的存在,然国常路大觉独赴德国成为黄金之王携石板归日,并成为唯一真正支配日本的王,国常路家随之壮大一枝独秀,五条家只能偏居一隅。于是五条家主蔽匿其身,转战商场,暗中则心存不满,觊觎石板和王权者之位,两方重重矛盾,枕戈待旦,只引而不发。
十多年前,迦具都事件爆发,以王权体系为主宰的日本,基本可以认作损失了四位王权者,已近耄耋的黄金之王国常路大觉见局势不稳,于是发心开始准备继承者王储之事。适逢对门世家五条一族诞下后人,且得到五条家主卜筮,婴孩大有大成就者之相,黄金之王深谙其理,一番斟酌后,便亲自登门拜访,提出将这个孩子纳作自己的氏族以作栽培。
那么你的条件呢,这种好事总不会平白无故地落下吧?五条家主问。
阴阳界天文道的卜筮观测在于因缘聚合、天人合一,一切只为搭建可能性,而在他对孩子的卜筮中,非常具相的一条即是,这孩子是匹未遇伯乐的千里马。国常路大觉率先登门拜访,可见卜筮中提到的伯乐,很有可能就是国常路大觉本人,如此,未来这个孩子,或将成为下一代黄金王权的适格者。
结果,黄金之王却说,条件简单,你的孙子既然由我来培养,那么就要直接过继给国常路家,你如今既投身商场,作为交换,我将国常路下辖餐饮行业股份的百分之十五拨给你。
其实,这种条件放在普通的商宦之家,自是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可放在与国常路家过去地位平等的阴阳师世家家主眼中,就是灭顶的侮辱。你这是让我卖孩子啊,钱我可以自己挣,可你让我把我的孙子过继给你,就是说要我的种——姓你国常路的姓,那不就等于揭了我五条家的底,断了我五条家的香火,你什么居心啊你,再者,真若跟了你的姓,这孩子未来再怎么大放异彩,照样光不了五条宗耀不了五条祖。然碍于黄金之王的强权,五条家主只能推脱说,再等等,再观察观察,毕竟孩子还小,要先养在亲爹亲妈身边才好。
之后每年除夕,黄金之王都会过来瞧瞧,看一看这个孩子,观一观他的命相,变着法还是想把孩子弄到自己身边。直到孩子四岁那年,黄金之王那边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总归他希望过继须久那到身边以进行异能者培养的计划就被搁置了,黄金之王亦再没和五条家主提过这件事。
于是在五条家主看来,好你个国常路大觉,你先是对我提出了近乎断子绝孙的侮辱性质的条件,我不好驳你的面子便稍作推脱,可这刚几年过去啊,你说不提这事儿就真不提了,成也是你败也是你,什么话都教你说了,什么事都教你干了,你也太给自己脸,太不把别人放眼里。至此,五条家主对黄金之王国常路大觉的不满更甚从前。
同年,五条家主通过关系,供养并会见了藏传佛教大德观音上师嘉瓦仁波切,就相关之事向其请教,最后得到“无常”“万变”及“静候佳缘”的相关建议。结果这一静候,便真等了好几载。
孩子从总角幼童长至舞勺之年,聪颖非凡,深得五条家主厚爱,不想,他竟兀端端受不了这个家族——离家出走了,最终误入到绿之族。绿之族诚然为非法氏族,五条家主断然首先想撇清干系,然绿之王主动与他联系,说会培养孩子。五条家主因而联想到孩子降生时所作卜筮的伯乐之说,再加上孩子四岁时嘉瓦仁波切的建议之言,便陡升信心。因为,若利用这一代绿之王以给予孩子深造异能的机会并取得石板,那么未来,无疑权力及最高荣誉皆将冠以五条之名。此乃运数之陡起。
谁知,一六年三月十四日,这一代绿之王发动神奈川事件,革命失败,宣告被俘。五条家主本是失望至极,然再一结合过去的占卜和当年嘉瓦仁波切的谏言——什么叫万变?他突然想到,或许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即是绿之王不错,然千里马的归属,却非为绿色,乃为最初错失的黄金。所以,五条家主现在的意思是,自己身为政治领袖,再以孩子的觉醒为契机,将王权体系与政治体系合二为一,即王政归一,未来皆纳在五条家族名下。想法是很好,然这就需要须久那为觉醒做出相应的心理及精神准备。
可是,对于须久那而言,明摆着把流弄出来才最要紧。他才不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和权力之纠呢。
十分钟已过,面膜的营养渐渐渗入肌理,紫轻轻地将它揭下。琴坂叫了几声,飞出窗外。
在发生了这许许多多事情后,须久那今天从爷爷那里得知了过去之事,并第一时间转告了自己,虽不知其中做没做隐瞒,但可见,这孩子果真是个能成大事知道以大局为重的,紫叹息。先前他的臆测也不错,五条家主手里另藏了一枚子,且匿有大阴谋。
那么流呢,流对黄金之王曾意图将须久那纳作黄金王权继承者之事,到底知不知道,是否早在“五条须久那”这个人成为JUNGLE的用户并晋级为J级干部后,流就是以利用为目的在……如此一想,事情便越来越莫测了,那还不如单单纯纯认作,比水流也不是完人,普天之下自有他也不知道的事。那么白银之王呢,作为第一王权者,白银之王知不知道、知道多少。而现下,流被关在白银之王的辖地内,会否通过白银之王知悉这些幕后之事,并对局势做出新的判断。
紫边琢磨边捏起一点嗓音,“小须久那,你知道为什么偏偏在你四岁那年,黄金之王便不再与你爷爷提过继之事了?”不等须久那开口,犹然自问自答,“按照时间推算,正是那年,流孤身一人去了御柱塔,挑战了黄金之王。当时我在场,流是圣域全开的状态,黄金之王亦全开圣域且身边围满氏族,流自是输了,但我想,正是这件事,令黄金之王生出警惕,认为幼年异能者不可信,太不稳定,而且异能者在幼年就被赋予过多期待,或压力过甚,会造成性格扭曲……然不论如何,须久那,真真因缘际会,后来你却到了流的身边,这事儿……”紫抿起嘴忍住笑意,“这事儿,怎么想怎么逗趣。”
他快憋出内伤了。
那方须久那哼唧两声没言语,似是不屑,似是对此巧合倍觉无聊。紫盼着波光粼粼的海,继续说:“现在我问问你的想法,对于这件事你分析了没,你怎么想,你觉得接下来你爷爷会怎么做?”
缓缓,孩子稚嫩的声音从终端那头传来。反正我已将我要近期行动的准备告知老头子了,我认为,老头虽然认为救流出来不一定有没有用,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个让我觉醒的好时机,因而——我只是猜测啊——他没准儿会以流为饵,在咱们展开行动并吸引了白银、赤、青三位王注意力后,发动军队及家臣攻占御柱塔。
紫敛起目光,“答对了。”
可我的想法不是这样,须久那说。我的想法是,由我和对石板图谋不轨的老家伙转移三位王对流的注意力,从而放空学园岛,再由你去……
“不行,”紫打断他,心头萌生黯然,“如果流知道你将成为黄金之王,且想到你爷爷的目标是在这次行动中拿下石板,那么,以流为饵,才是流会选择的正解。”
须久那兴味索然地嘟嘟哝哝。仿佛他也知道,流确实会这么选,便再没了先前能旗开得胜的快意。于是在他嚼了几句闲话后,紫听到他说,那问题来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定在什么时候,上回流利用蓝服传出地点范围,大约这次流会利用白银将时间段传出来?
“对的。我已遣线人在学园岛围观动向,以盯紧白银之王。”
时间在大地上肃静地流淌。矮墙颓圮,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支楞些杂草,橘子树下的秋千有一搭没一搭地摇荡。旭日高昇的好天气,初夏还未浮生的热气沉在海平线外,暖阳温吞,斑斑驳驳将树影切得细碎,流水般倾泻进来,让整个家都染上温婉的色泽。生怕一片荒芜中,谁不知道他们即将团圆似的。
“要打开异能限制环并非难事,”木村坐于床边悄言细语,“只是,宗像室长那边即刻会有警报。”
流说:“好的,谢谢,这便够了。”
他笑着,这笑是有些温柔的笑。比水流其人骨子里的偏执倔强,像神奈川的雨一样,奇怪的消停了。
学园岛上,凉风泫然而起,林间野草开花,苍败倒伏,几片叶子在风眼里打着旋儿。未及小满节气,海岛楚雨磅生,将草与叶浸得湿润。雨落泥,泥生花,花花不过指尖沙,尘归尘,土归土,尔归何处,我心难悟,或可为尔祈福。
————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情感口述故事
本文标题:
文章链接:men.ngnvip.com
文章来源:女娲之汉
友情链接:✅女娲导航 ✅恋爱之书 ✅健康笔记 商务笔记 ✅健康杂志 ✅分享笔记 ✅健康社区